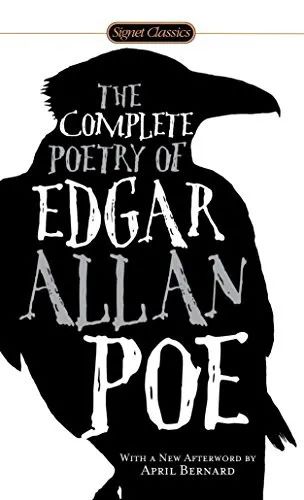东北、穷鬼乐园、仙症:作家郑执的文字世界


独家抢先看
“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我必须写下去,也只能写下去,不存在别的救赎。”——郑执
近两年,一批东北新生代作家让“东北文艺复兴”成为了一种现象。但在“东北叙事”之后,作家们已经开始寻找新的表达——作家郑执就是其中一位。
郑执,沈阳人,作家、编剧,已出版长篇小说《浮》《生吞》,2018年凭借短篇小说《仙症》获得“匿名作家计划”首奖,最新出版小说集《仙症》。
郑执在访谈中称自己为“过山车型作家”,以形容各个阶段的作品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仙症》中富有节奏感的文字、多线交错的情节、具有北方凌冽气质的人物,以及东北民间信仰元素,都曾经令很多读者感到震撼。在北京,我们与郑执进行了一场关于文学的对谈。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郑执都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作者,而眼前这本《仙症》,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 | 苏炜
✎编辑 | 程迟
2018年12月,一场名为“匿名作家计划”的比赛揭晓结果,郑执凭借短篇小说《仙症》,从三十多位匿名参赛的作家中脱颖而出,摘得首奖。
站上颁奖台,郑执的获奖感言也与其他作家不大一样,他说,许多已经成名的作家,借着匿名的机会,勇敢地抛弃过往的风格,以新面目示人,但自己不需要被重新认识,“就希望大家认识一下”。
获奖次日,郑执接到了一席的演讲邀约,他脑子一热,痛快答应,旋即有些后悔。“(一席)通常上去一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我能带给大家什么呢?一个作家,上去教人写作吧,我也没这种资格,而且大家也不爱听。”
郑执在一席名为《面与乐园》的演讲,让更多人认识了他。图/一席
最后,郑执把一段有关家庭和故乡的往事搬上演讲台,题目是《面与乐园》。“面”是他父亲曾经经营的一家小面馆,“乐园”是他在家乡沈阳,常去光顾的一家廉价啤酒屋,其中流连的多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们。
讲述的开头,东北人郑执依旧展示了一把东北式的幽默:
“我叫郑执,31岁,沈阳人,是一个职业作家,主要写小说,缺钱的时候就会写剧本。邀请我来演讲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我在去年12月份的一个文学赛事上拿到首奖的第二天,所以不得不让我认为,社会有的时候稍微势力眼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台下笑声掺杂着掌声,郑执由此真的被越来越多人认识了。
东北,沈阳,穷鬼乐园
按照大多数普通中国家庭的视角来看,郑执之前的经历够得上波折,但这样的家 庭故事镶嵌在世纪末东北社会的大背景下,似乎也显得平常——
十八岁时,郑执的父亲上山下乡归来,接了祖父的班,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九十年代初,市场大潮的最前浪尚未抵达东北,但父亲已经察觉到即将到来的衰落,他辞职下海,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沈阳北站开了一家抻面馆,走薄利多销路线。
生活中的好运和厄运互相交织,面馆生意曾迎来高峰,但最终跌入低谷,郑执自己考入省重点高中,高考超过一本线,又因为英语成绩突出,通过香港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在2006年南下读书。
大三的时候,父亲患重病,父子间终于达成了彼此间的某种理解。父亲去世后,郑执选择休学,回到沈阳生活了一年,他告诉我们,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开始真正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
与很多传统作家不同,家乡沈阳或许远算不上郑执的文学原乡,在这里,他少年时的社会关系稀薄,甚至找不到多少可以聚饮的人。重点中学毕业的同学们大都分散在北上广深,还有一些定居国外。
郑执告诉我们:“我十八岁离开沈阳以前,真的就是从学校到家,过着一种两点一线的生活。直到离开以后,我才突然想到沈阳有好几个区,我都没去过。”
重返沈阳那一年,郑执迫切地想要对这座城市多一些了解。每天除了健身、做饭、读书写作,以及陪母亲看电视剧以外,还空下大量时间,郑执给自己制定了出行计划:坐哪趟公交车,在哪一站下车,到那些从来不熟悉的城市角落去走一走,看一看。
“穷鬼乐园”成为了郑执的灵感源泉。图/郑执
“穷鬼乐园”成为郑执这段时间里的发现之一,他第一次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走进这个父亲曾经光顾的地方,点上一瓶啤酒,观察周遭那些“运气不好一生都很难再爬起来”的人。
在演讲中,郑执用文学化的语言,翻译了一下老板娘对穷鬼乐园定位的描述:如果此地终会消亡,这些灵魂又将何处安放?
一年后,郑执暂时告别那些游荡在北方的灵魂,回到香港,靠着高利贷完成学业后,最终成为一个以文字为职业的人。
《仙症》前传
2018年初,郑执收到约稿邀请,他爽快答应,却还不知道这会是一场比赛。稿子拖了半年之久,郑执再次接到编辑的催促,才得知这次要写作一篇参赛作品,于是在一天一夜之间完成,把这个在脑海中盘踞十年的故事,化作一篇《仙症》。
《仙症》
郑执 著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10
“倒数第二次见到王战团,他正在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只用两腿封堵住柏油路段,右臂挥舞起协勤的小黄旗,左臂在半空中打出前进手势,口衔一枚钢哨,朝反方向拼命地吹。刺猬的身高瞄不见他的手势,却似在片晌间读懂了那声哨语,猛地调转它尖细的头,一口气从街心奔向街的东侧,跃上路牙,没入矮栎丛中……”
这个奇诡的开篇,一下子将读者带入到故事中去,评委苏童甚至褒扬道:“这是我在国内看到的写精神病人最像的。”
尽管以文学学位毕业,但郑执坚决否认自己学院派的身份。和许多作家比起来,他的阅读和写作经历,都显得相对纷乱。郑执成长的九十年代,学英语正成为一种潮流,母亲把他带到沈阳外文书店,要他自己选书、买书。
偌大的书店,几乎都是英文书籍,郑执讨巧地选了外文书店出版的世界名著——这套书是中英对照版,一半中文,一半英文,虽然翻译水准参差不齐,但他还是就此完成了与爱伦坡的初次相遇。
The Complete Poetry of Edgar Allan Poe
Edgar Allan Poe
Signet Classics
“我在那之前,没有看过别人这么写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从那以后,“讲好一个故事”始终是郑执写作的核心追求。
在《仙症》之前,郑执已经出版过几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些走心,有些不走心”。
2017年写作《生吞》之前,郑执出版了一本销量惨淡的书,恰逢当时生活困顿,他对《生吞》寄予的希望是“大多数读者能看的书”,在类型化和文学性之间找一种平衡。
故事最初在App上连载,每更新一段,都能得到读者的评价,面对这些评价,郑执选择“自我审查”,删去一些“过于文学化”的表达。他说,未来想出版修订版的《生吞》,把那些删去的“私货”加回去。
《生吞》销量不错,但面对一些来自评论家和资深读者的批评,郑执还是有些不甘心。偶然写就的王战团的故事,让他下决心不受干扰地写作,终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本以《仙症》命名的小说集。
“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
《仙症》一共包含六篇小说,除了包括《仙症》在内的五篇短篇小说之外,还有《森中有林》一篇中篇小说。
故事的场景,有的依然在东北,比如《他心通》一篇,仍有熟悉的地域信仰元素;还有的已经搬移到了北京,比如《霹雳》一篇,描述了高楼与高楼、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凯旋门》一篇,是典型的“小城失败故事”;《蒙地卡罗食人记》一篇,则在结尾化为东北严冬纷飞的雪花,旋转飞升,转向魔幻。
篇幅最长的《森中有林》,郑执写了三个月,中间吸纳了数位编辑的建议。跨越三代人的故事,让几种命运以不同的方式连接,构成一个闭环。
写到第三代人吕旷时,郑执将他设置成一个出生在世纪末的“准00后”、转战于短视频软件和B站之间的“up主”。比照作者自己,人物年轻了十几岁,为此,郑执虚心地找到自己的两位小外甥女,向她们问询00后生活的种种,以此捕捉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的特质。
在后记里,郑执还是格外坦诚:
“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
《生吞》
郑执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11
他简单梳理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坦白写过很多短的轻浮的谄媚的,懒动脑也不走心的“那种东西”。如今,亲手杀死过的文学又再度复活,郑执说这一本“权当新的开始,给自己,也给新老读者们一个交代。”
在采访中,郑执说自己是一个“过山车型作家”,作品风格和水平起伏不定。但无论经过怎样的起伏,过山车仍在一条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如同后记结尾他所写:“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我必须写下去,也只能写下去,不存在别的救赎。”
又如《森中有林》末尾里,小说人物所言:“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
对谈,关于“那种东西”
硬核读书会: 你怎么评价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和新生代“东北作家群”?
郑执: 我一直认为,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今年接受访谈时,还是会收到这个问题。它是否构成一种文学思潮,一定是有人该去做的工作,但并不是我需要思考的事。当评论界和读者意识到某种趋势,而去讨论,这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个人的影响应该不大。我觉得看到不同比看到共同更有价值,当然总体来说,因为形成话题而收获更多关注、更多读者,是一件好事。
硬核读书会: 在选择写作以后,你的文学审美取向主要从何而来?
郑执: 从开始读小说到写小说,我无法抗拒的小说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好好地讲了一个故事。我大学生涯的后半段,因为休学,已经几乎不再是学生心态,天天想着怎么赚钱。
《我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跟随余光中夫妇的游屐,牵引出诗人的乡愁、文学启蒙、写作风格与文坛交游。图/豆瓣
在香港的最后一年,我修了一门课,有一节课会放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那一天恰好放到余光中一集,其中余光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让我得以清楚地向别人形容我的文学审美取向:“最忌讳用晦涩包装深刻。”
原来这就是我的审美,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如此精确的形容,后面的纪录片每隔一段时间,就读一段余光中的诗,我一直在哭。在那之后,我翻汪曾祺、老舍、史铁生,我发现我小时候没有读懂他们,我发现原来这就是最好的中文。
硬核读书会: 你在么看待你自己所写过的所谓不走心的“那种东西”?
郑执: 它们在文学上几乎没有价值,但对我个人的创作经历而言,却有巨大价值。那一步跨过来,我才明白所谓商业写作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今天摆正心态,各种条件允许时,我才可以摆脱束缚,清楚地与那些东西相隔绝。
硬核读书会: 你觉得现在对于写作是一个好时代吗?
郑执: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作者的包袱更少一些,所谓的对文学、对时代的责任感,现在可以非常坦然地卸掉。在这个方面来说是个好时代。但总的来说,在各种艺术的门类中,今天肯定不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一开始我有些悲伤,但之后心态就变平和了。一段命运的兴衰起落,是世间的规律,文学曾经有过那样的黄金时代,那么今天的“落”也没有问题。
专访视频
新周刊·硬核读书会专访郑执
采访:苏炜
剪辑:陈卓贤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