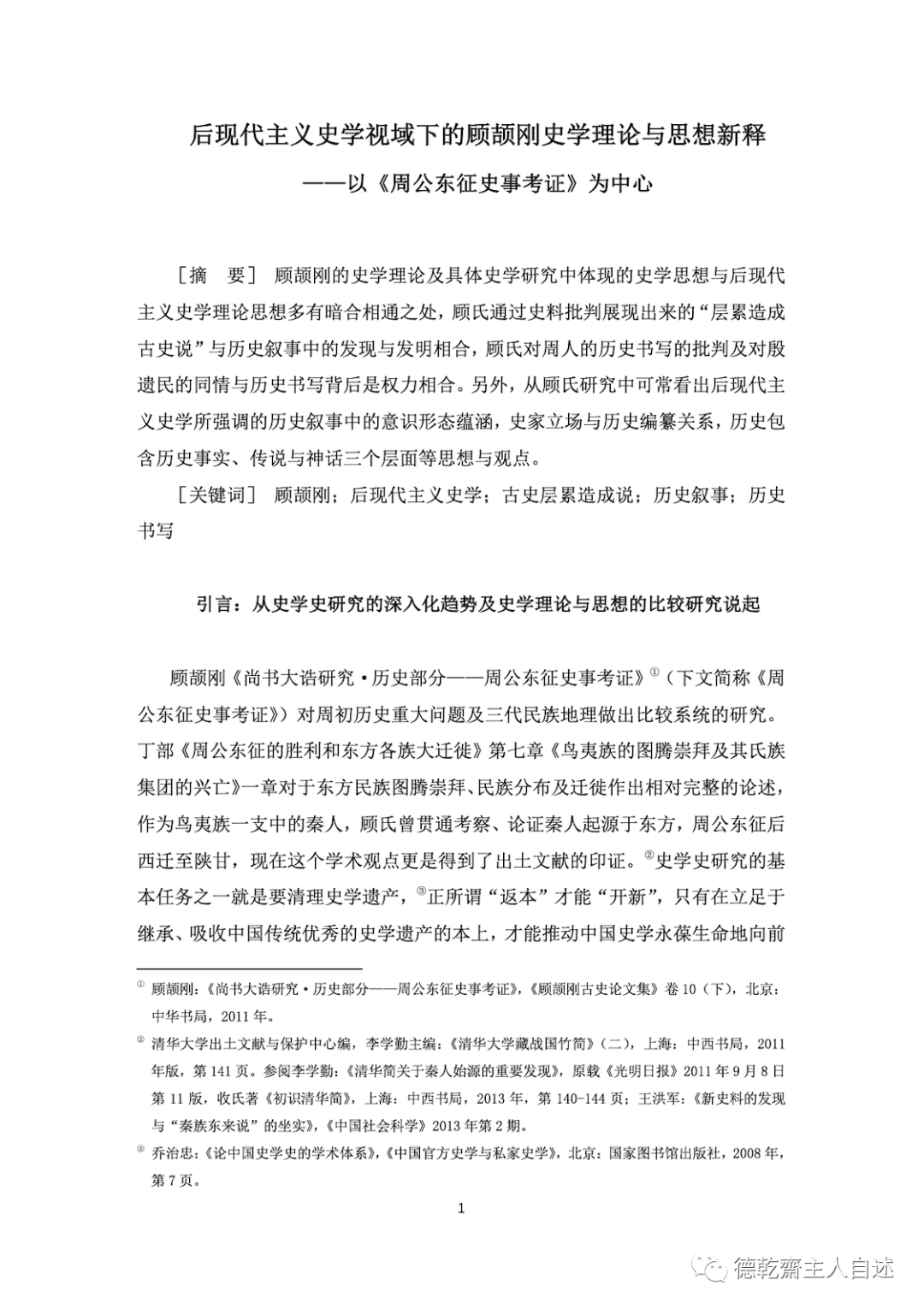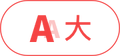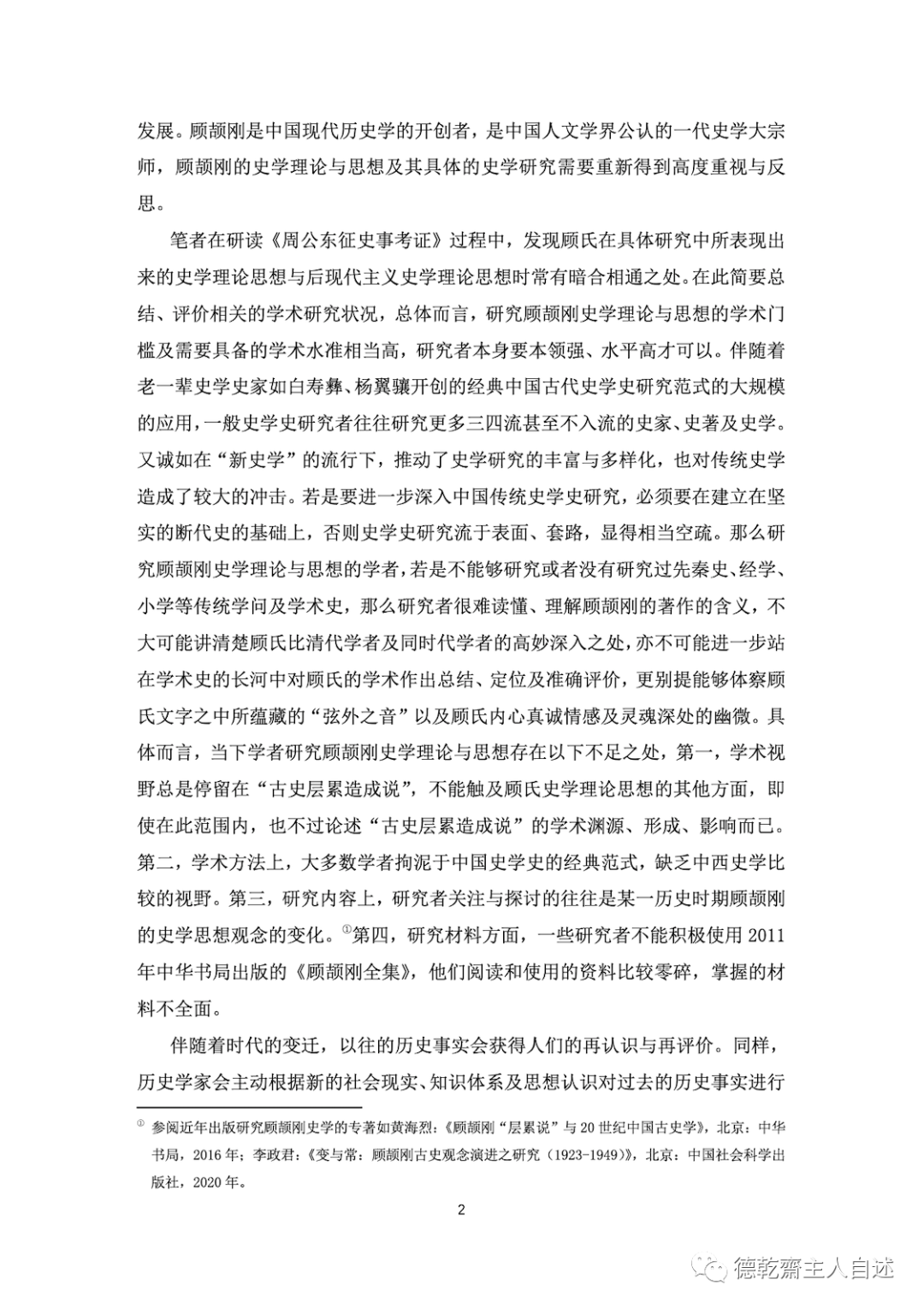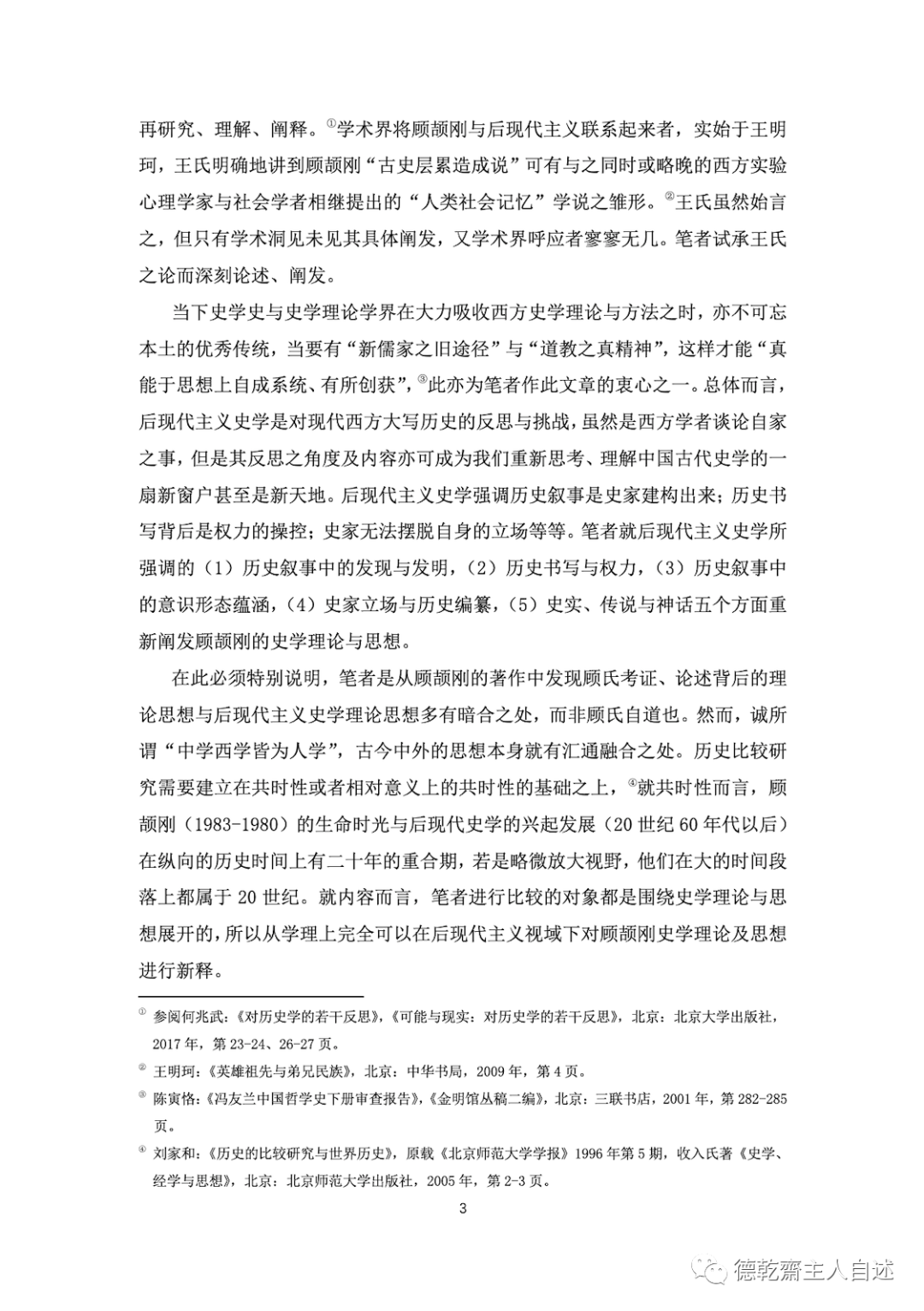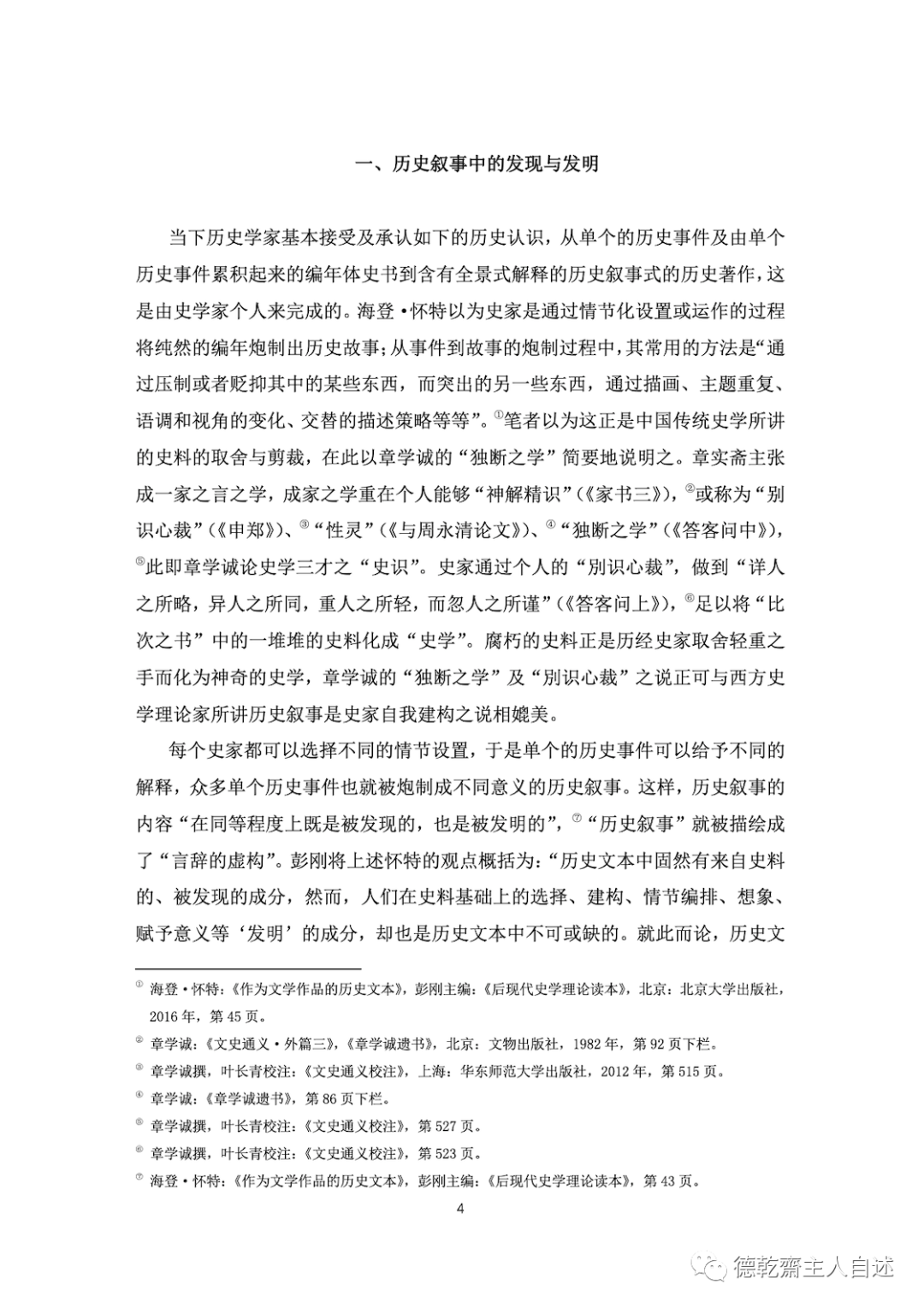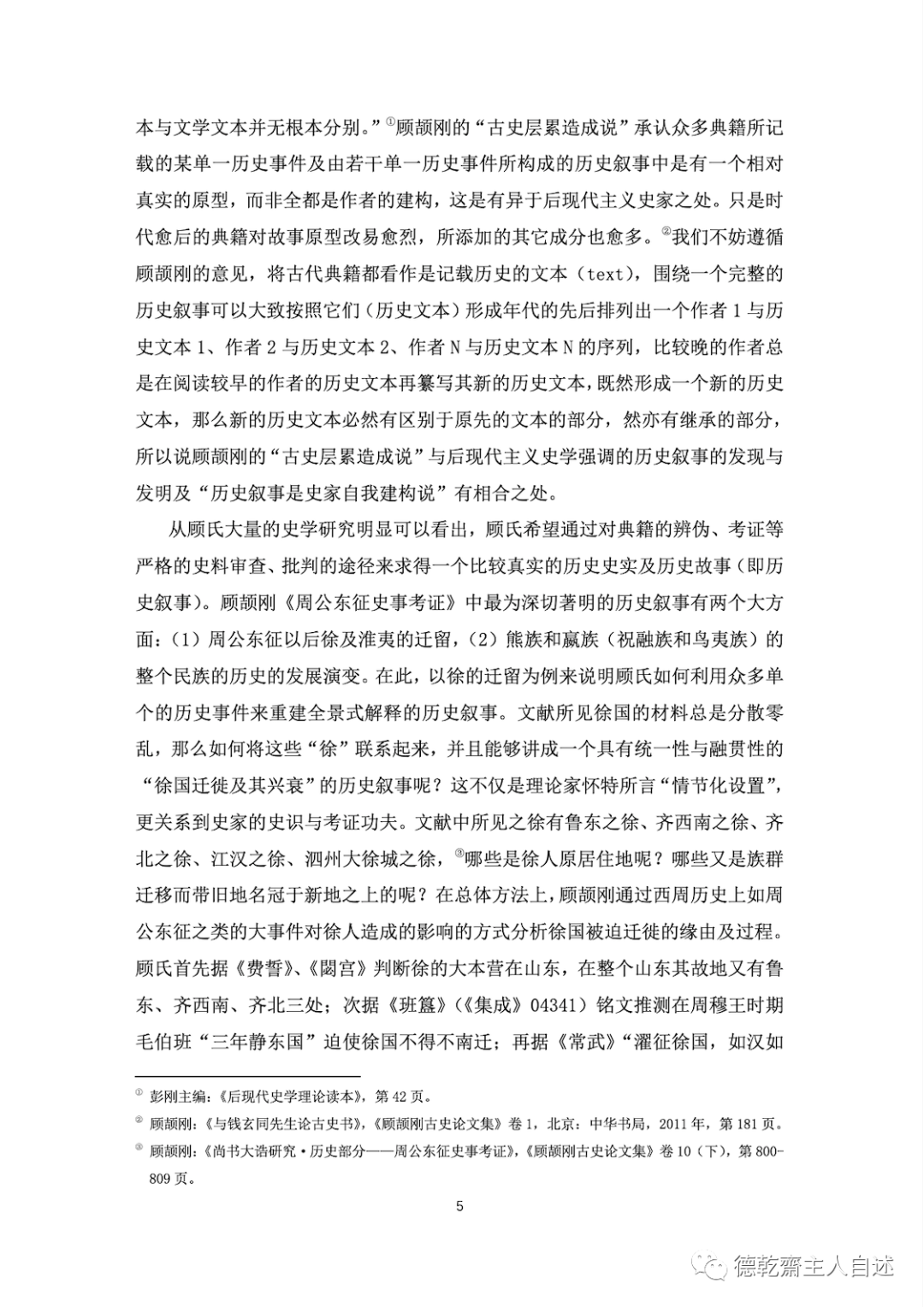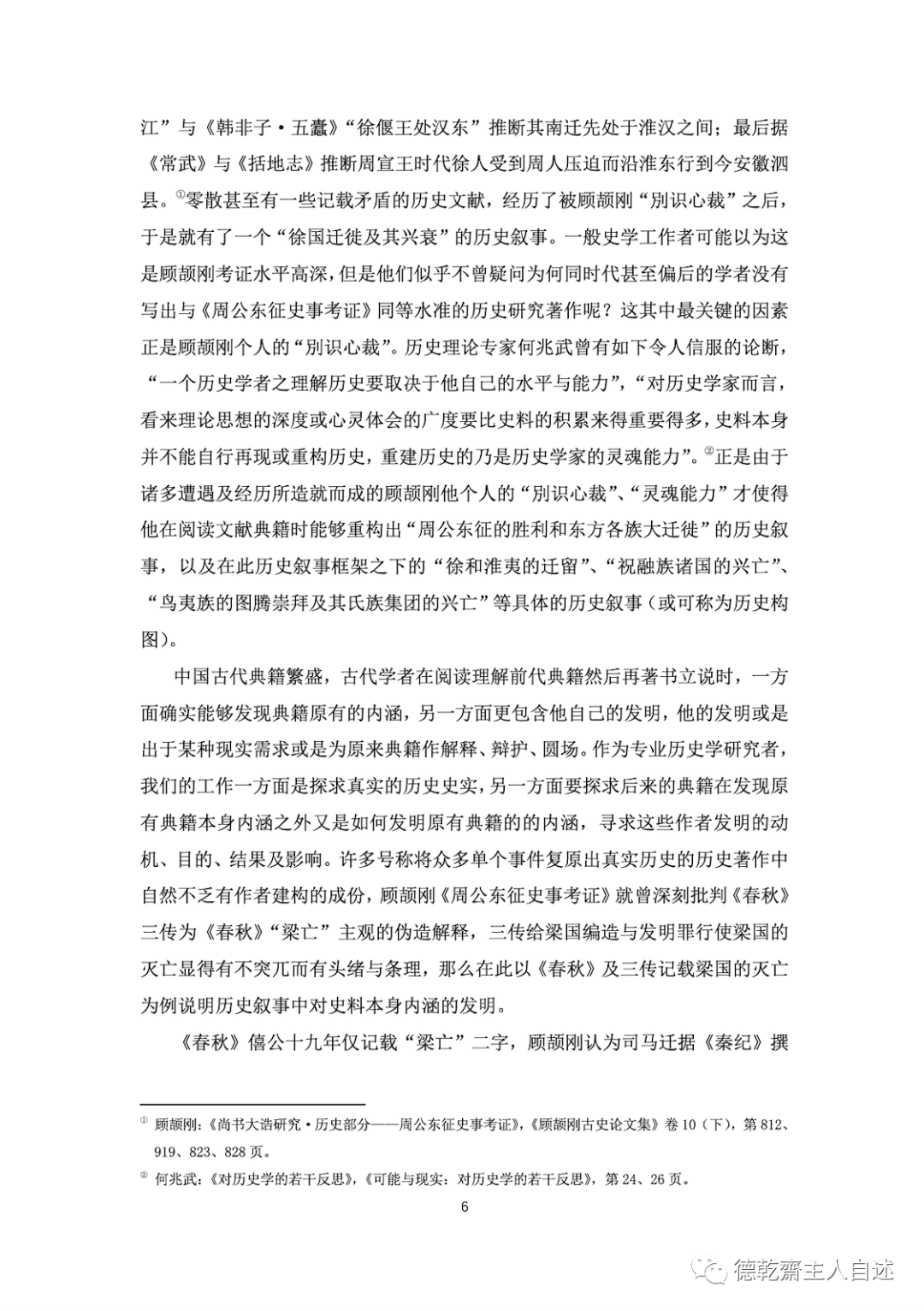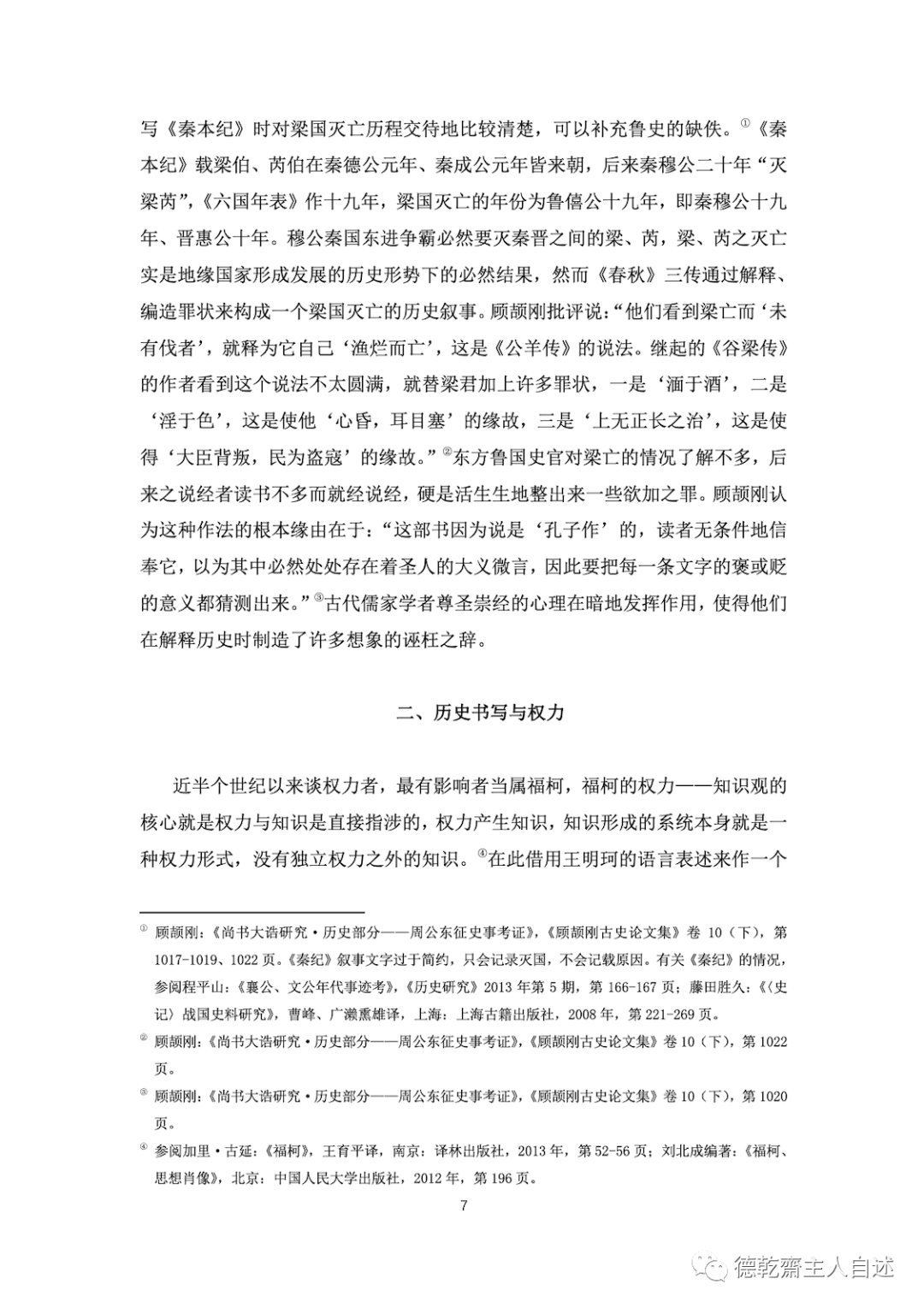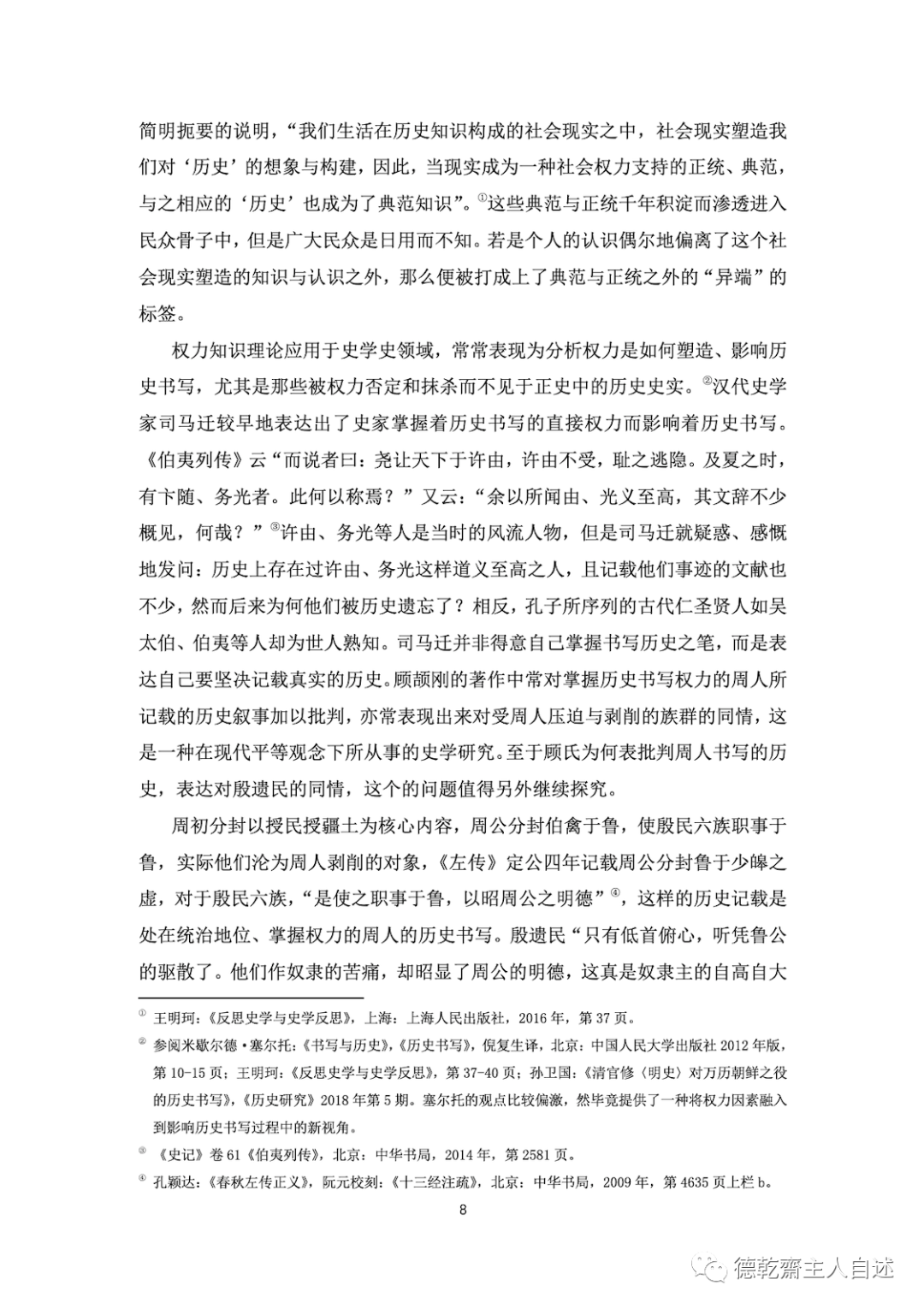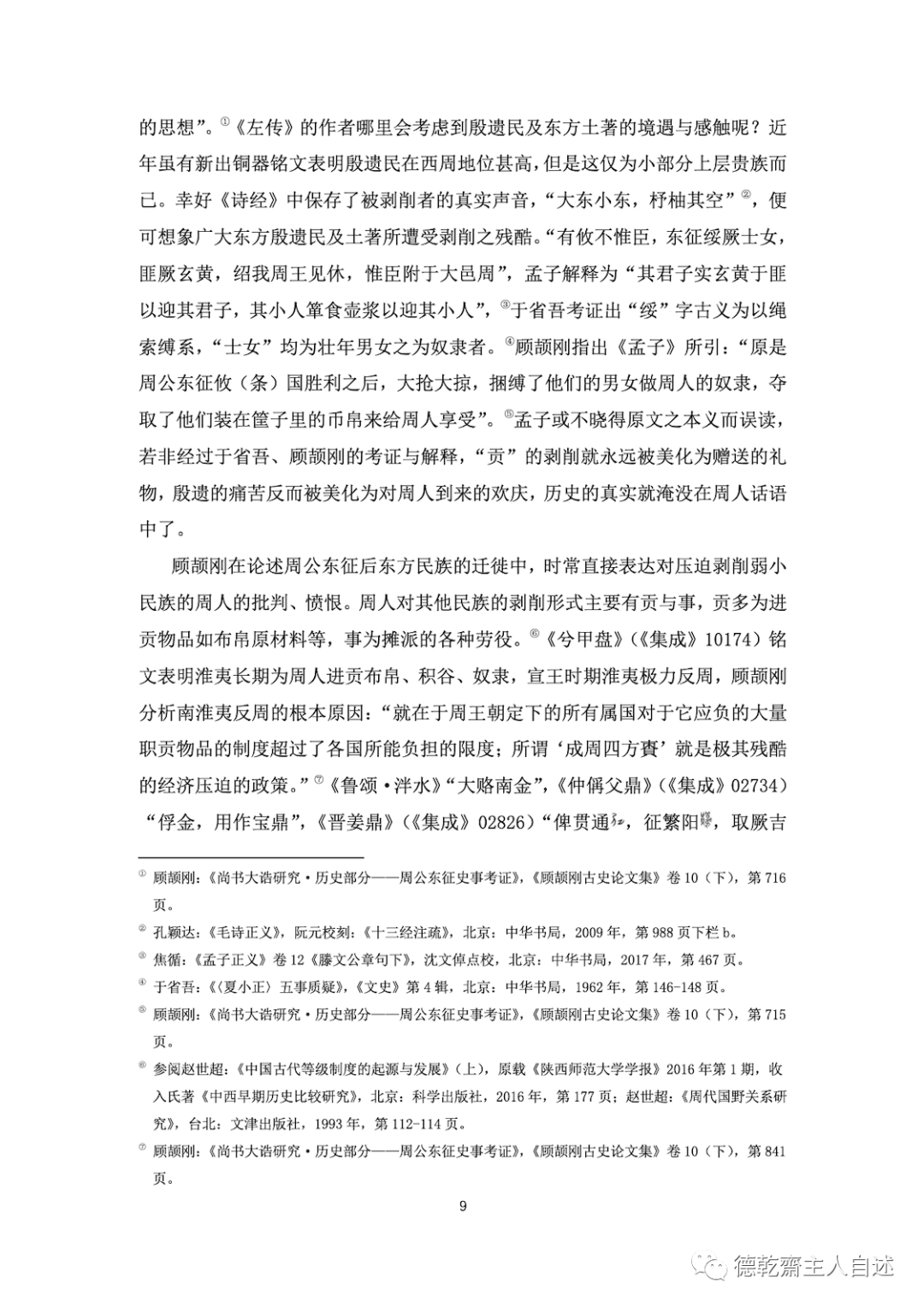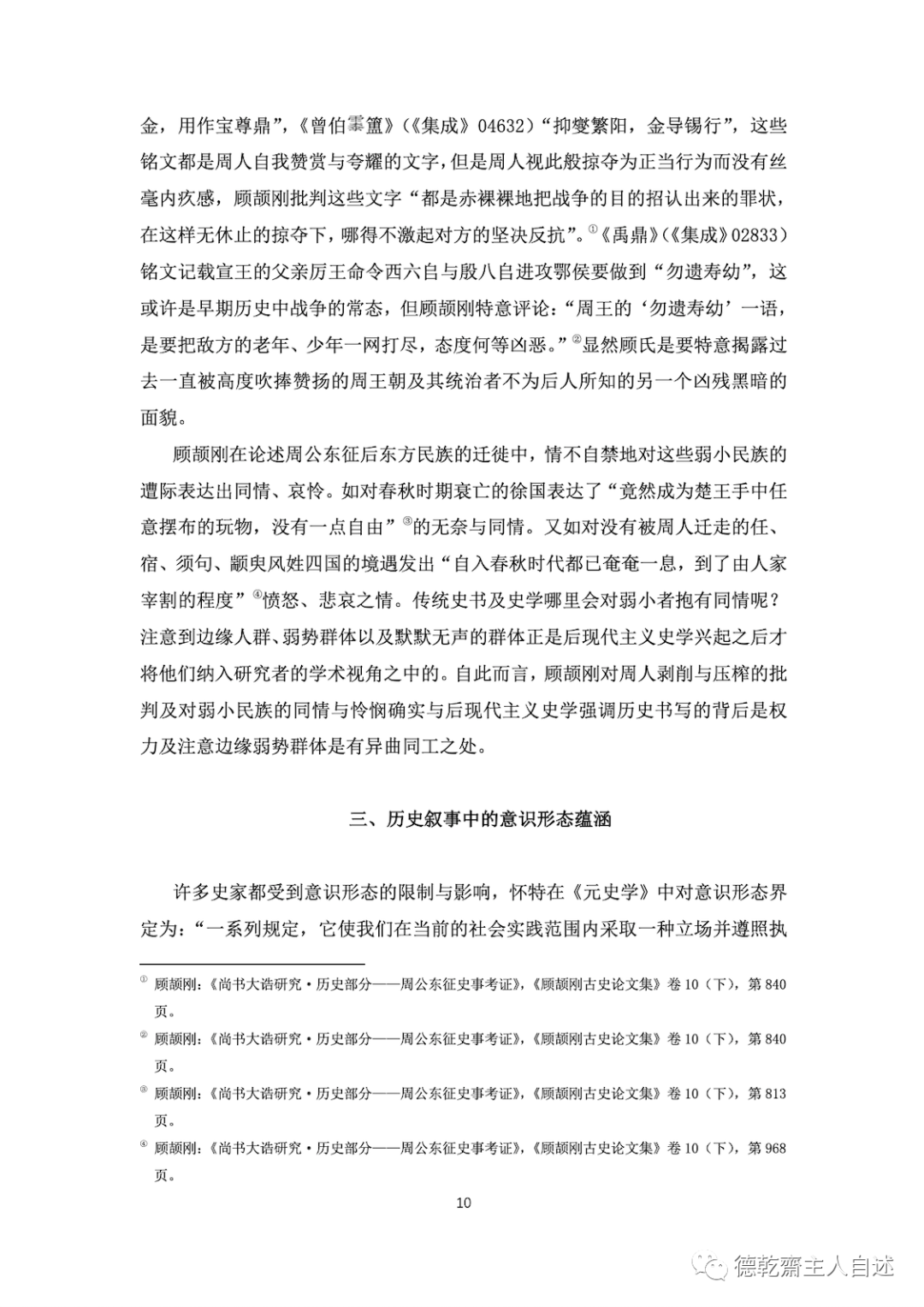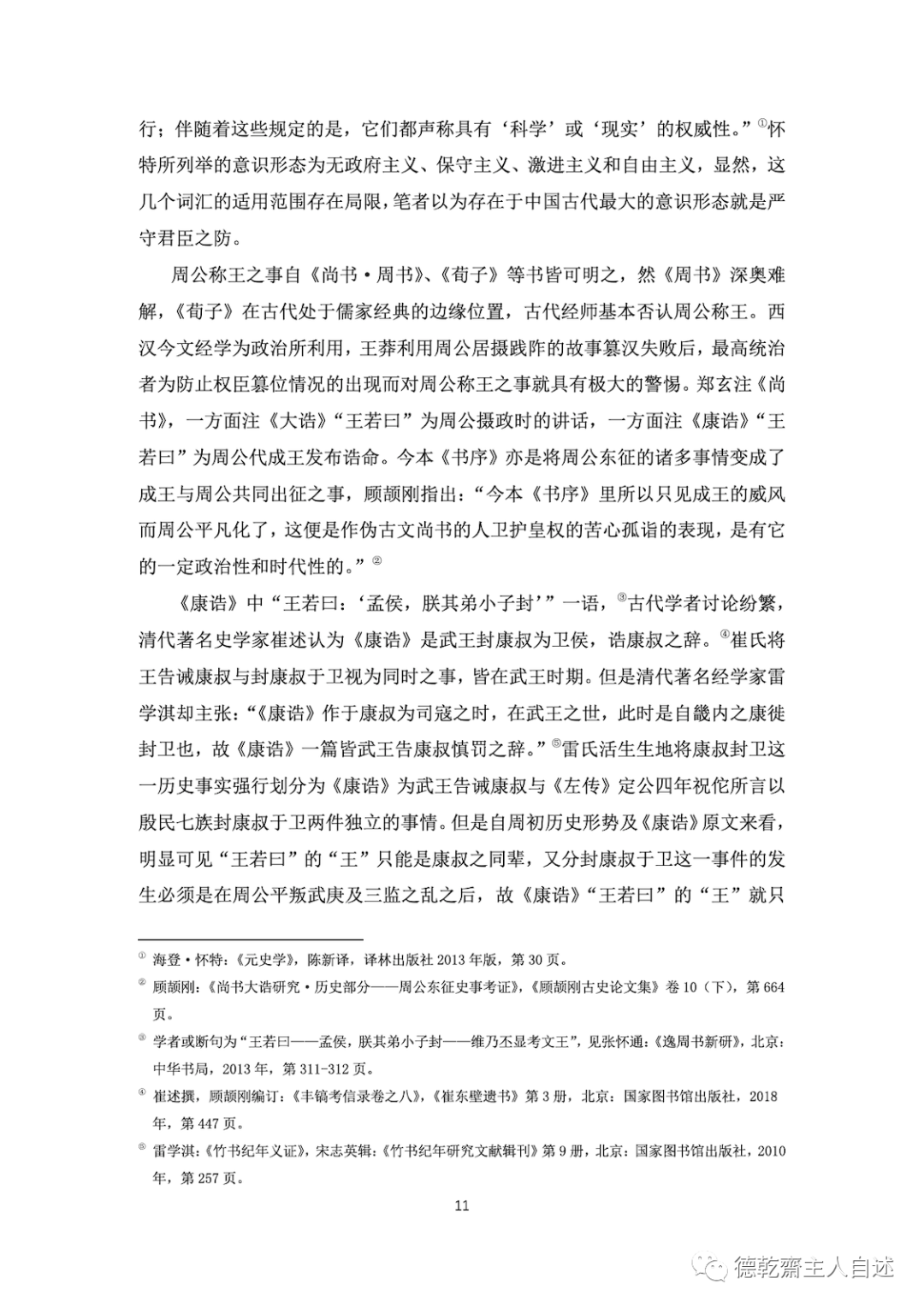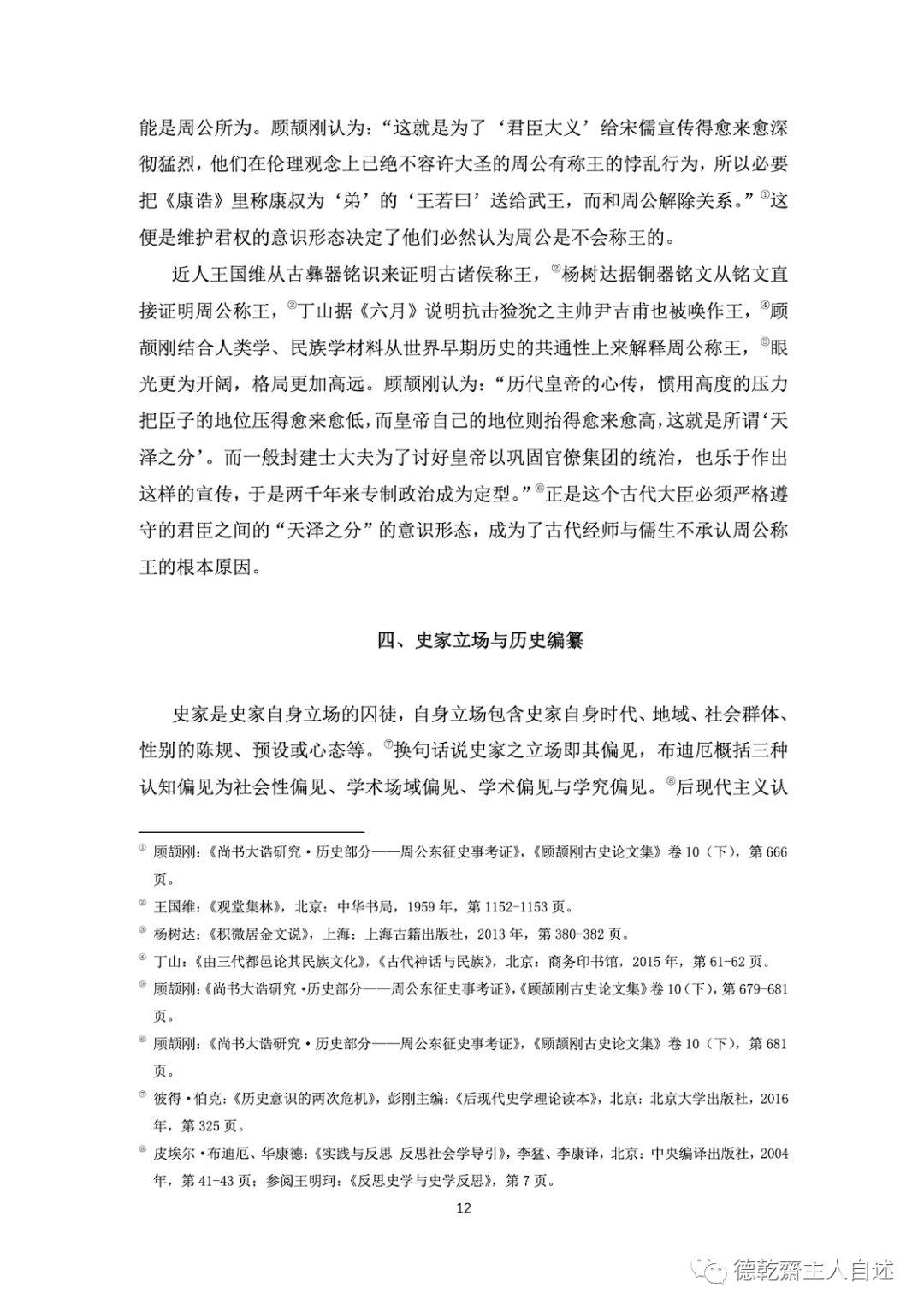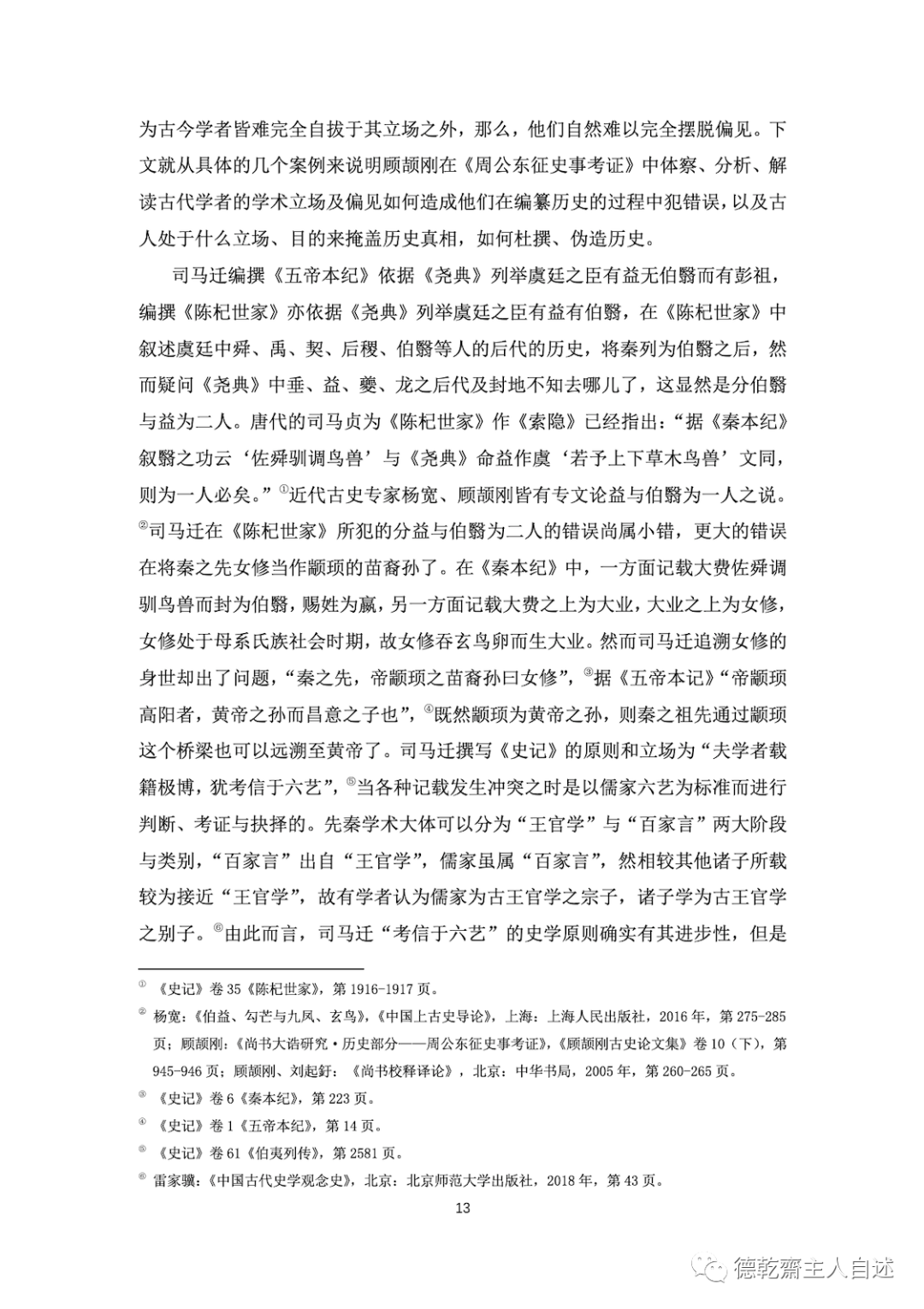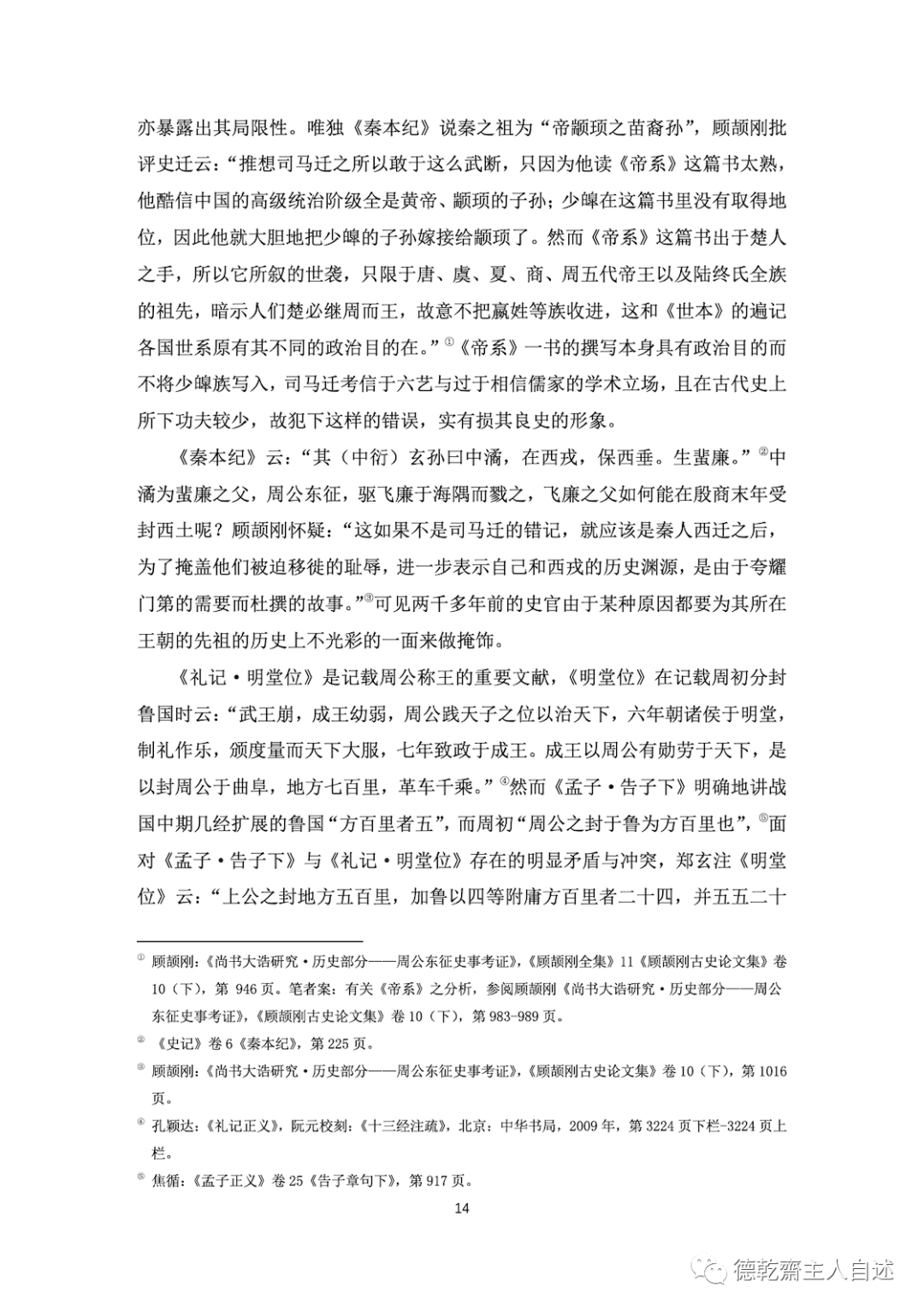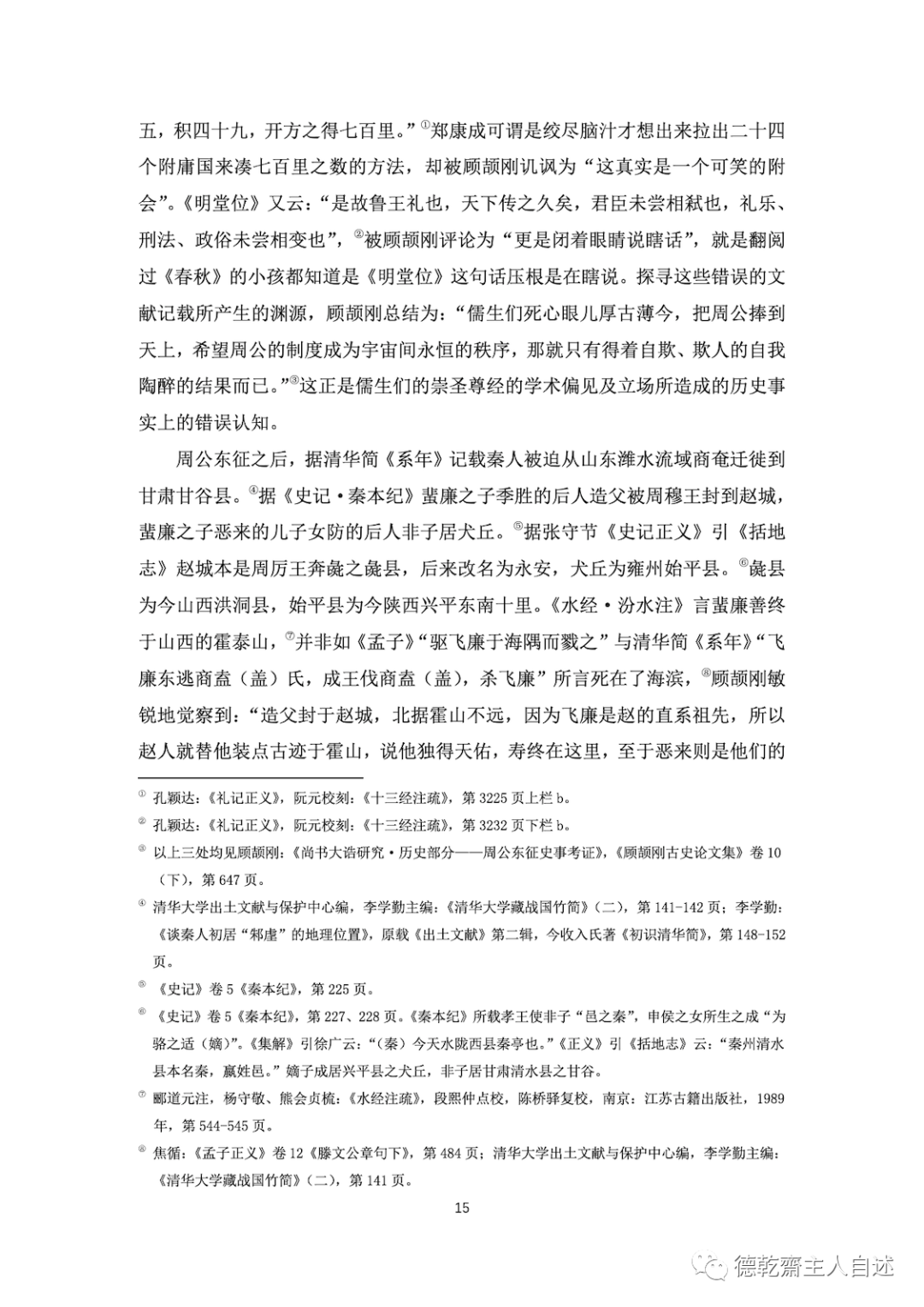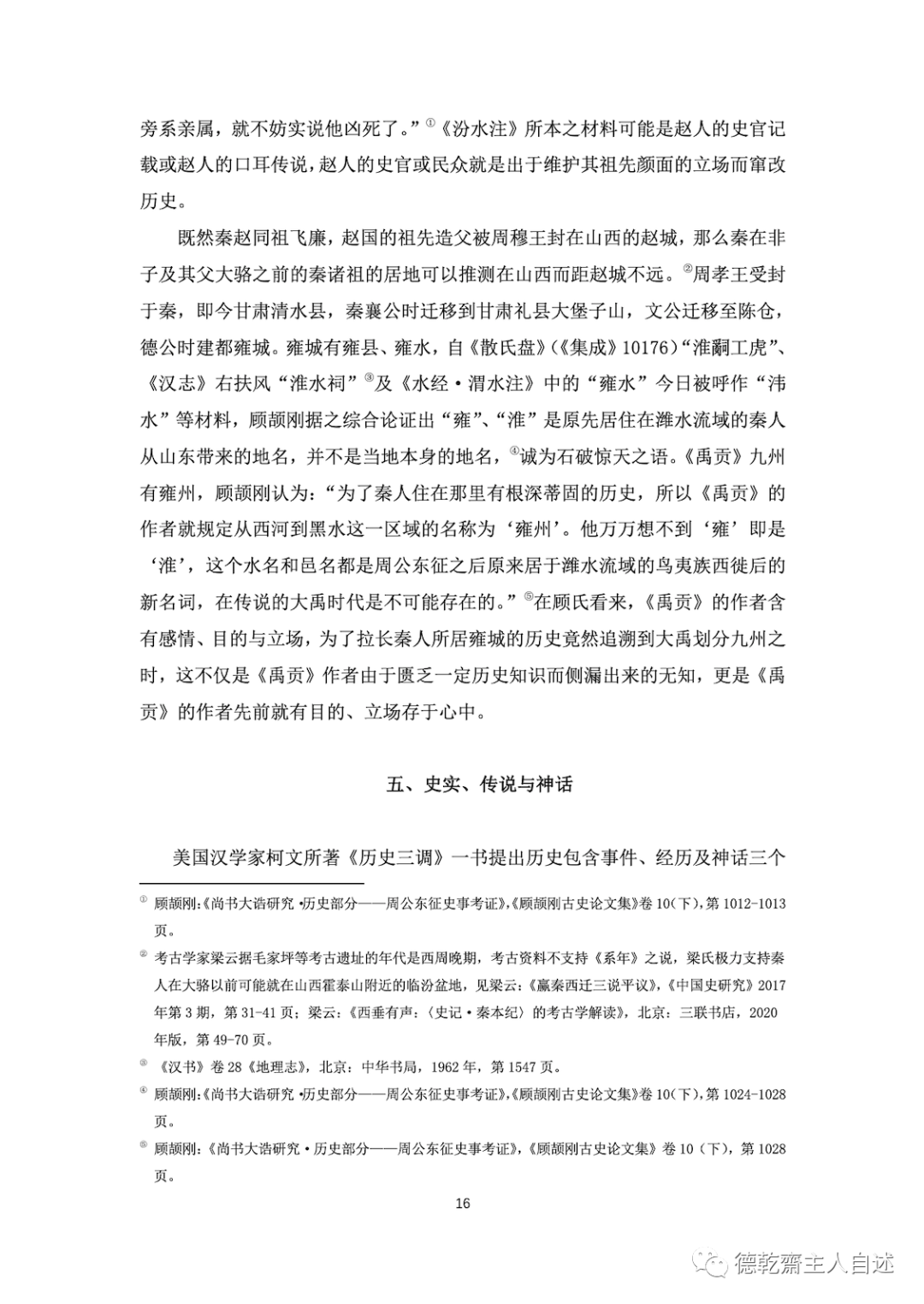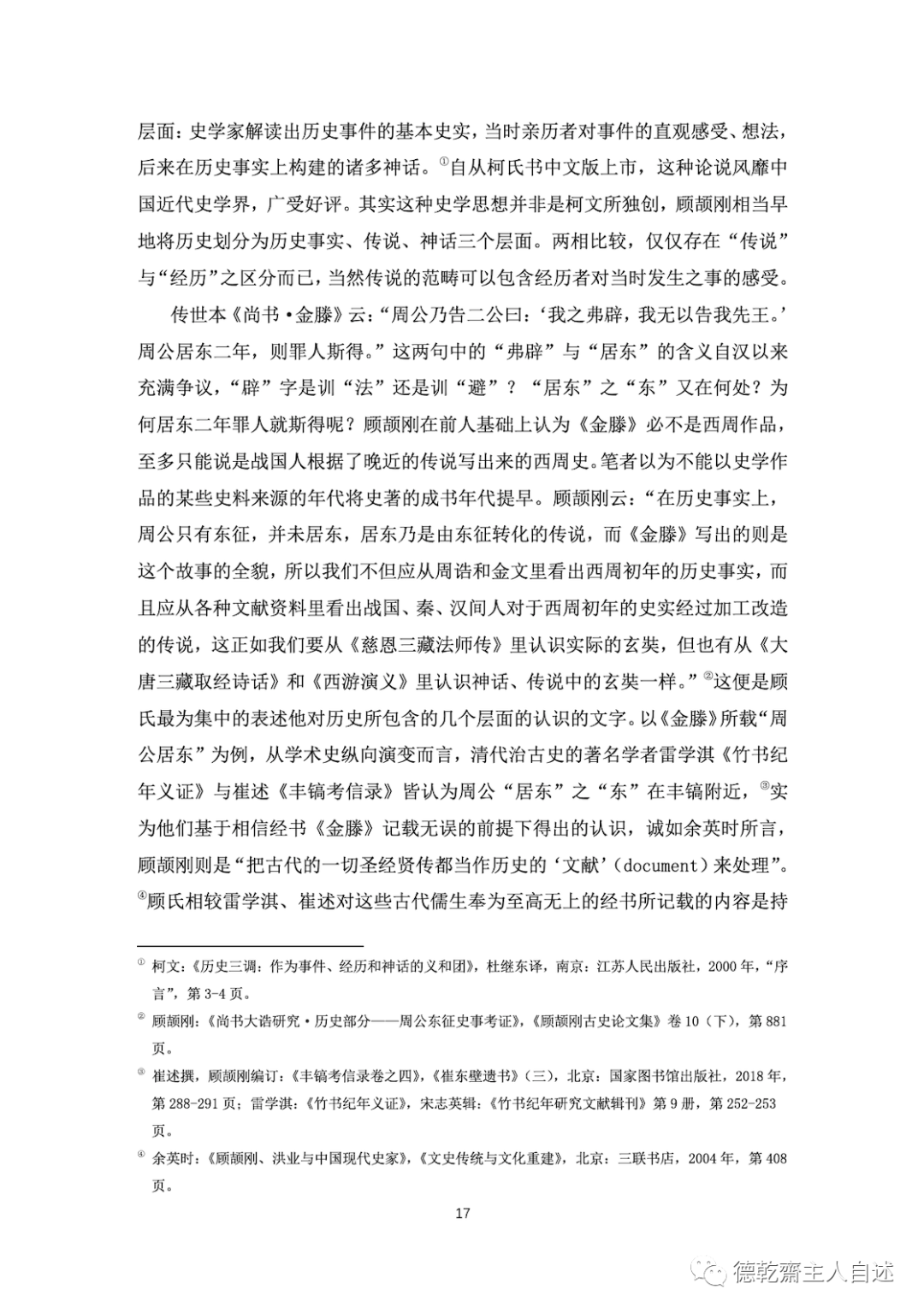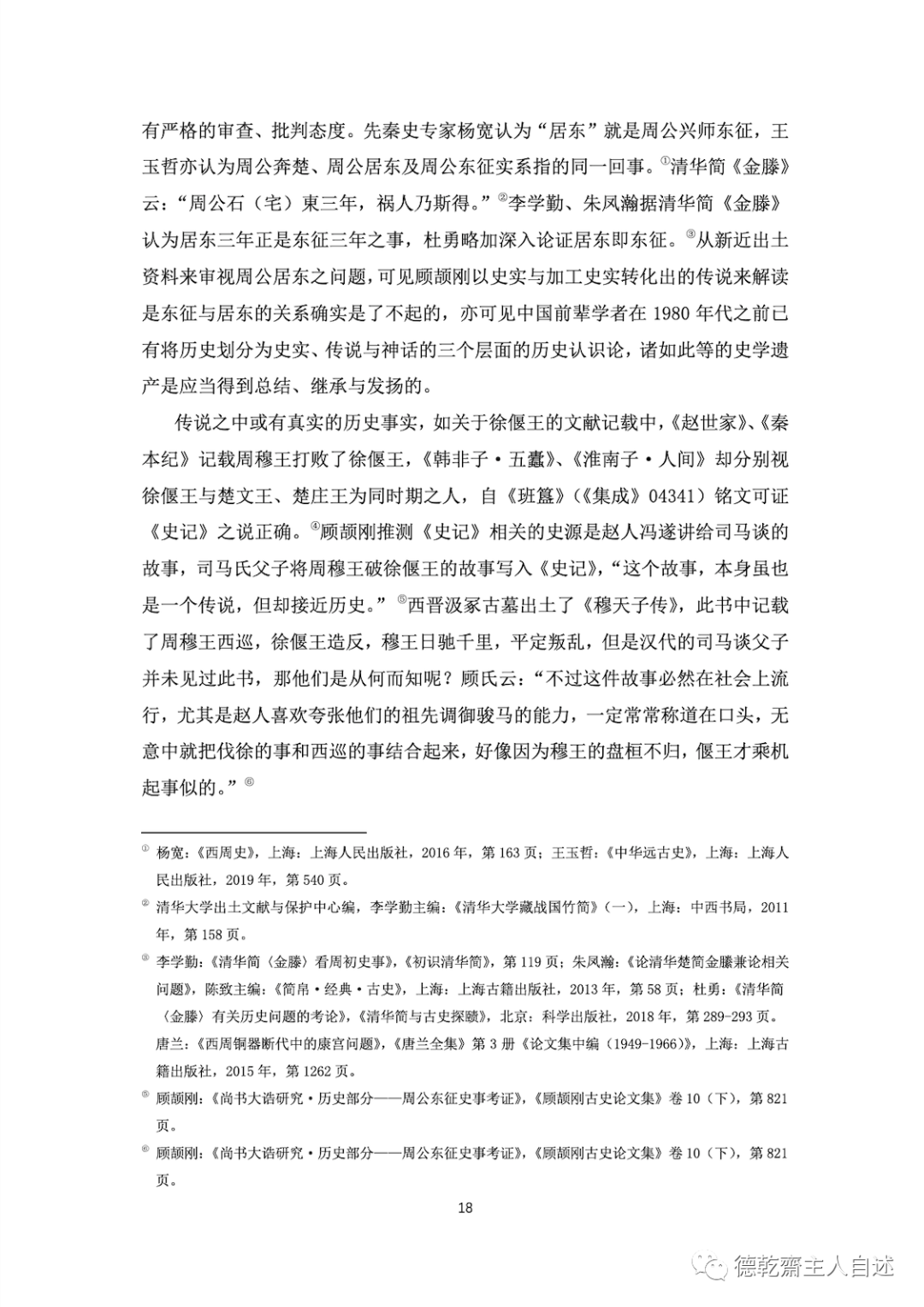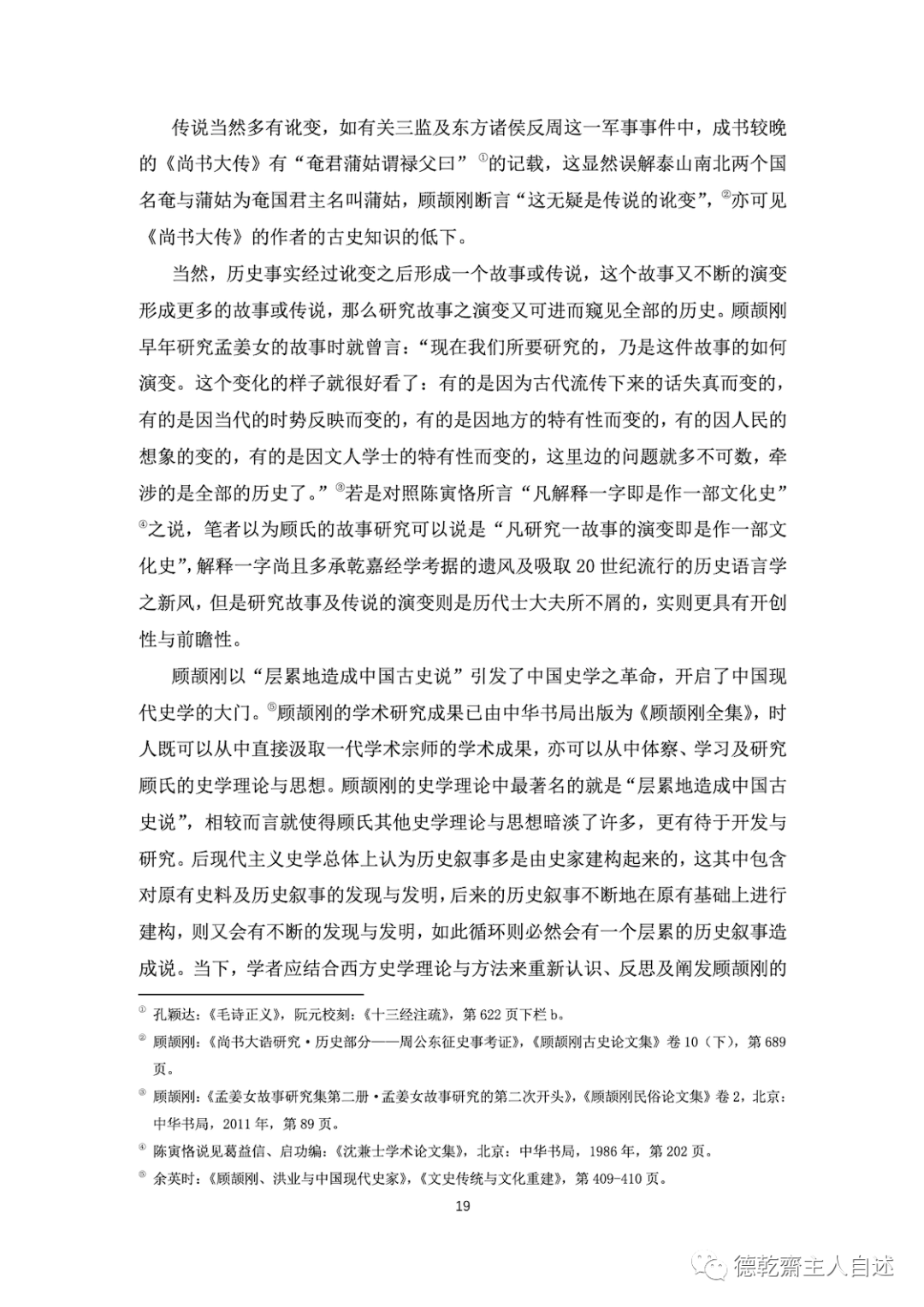【作者简介】张靖(1994—),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2016),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2019)。
后现代主义史学视域下的顾颉刚史学理论与思想新释
——以《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为中心
【摘 要】 顾颉刚的史学理论及具体史学研究中体现的史学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多有暗合相通之处,顾氏通过史料批判展现出来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与历史叙事中的发现与发明相合,顾氏对周人的历史书写的批判及对殷遗民的同情与历史书写背后是权力相合。另外,从顾氏研究中可常看出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强调的历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蕴涵,史家立场与历史编纂关系,历史包含历史事实、传说与神话三个层面等思想与观点。
【关键词】 顾颉刚;后现代主义史学;古史层累造成说;历史叙事;历史书写
引言:从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化趋势及史学理论与思想的比较研究说起
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1](下文简称《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对周初历史重大问题及三代民族地理做出比较系统的研究。丁部《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第七章《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一章对于东方民族图腾崇拜、民族分布及迁徙作出相对完整的论述,作为鸟夷族一支中的秦人,顾氏曾贯通考察、论证秦人起源于东方,周公东征后西迁至陕甘,现在这个学术观点更是得到了出土文献的印证。[2]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清理史学遗产,[3]正所谓“返本”才能“开新”,只有在立足于继承、吸收中国传统优秀的史学遗产的本上,才能推动中国史学永葆生命地向前发展。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创者,是中国人文学界公认的一代史学大宗师,顾颉刚的史学理论与思想及其具体的史学研究需要重新得到高度重视与反思。
笔者在研读《周公东征史事考证》过程中,发现顾氏在具体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史学理论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思想时常有暗合相通之处。在此简要总结、评价相关的学术研究状况,总体而言,研究顾颉刚史学理论与思想的学术门槛及需要具备的学术水准相当高,研究者本身要本领强、水平高才可以。伴随着老一辈史学史家如白寿彝、杨翼骧开创的经典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大规模的应用,一般史学史研究者往往研究更多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史家、史著及史学。又诚如在“新史学”的流行下,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丰富与多样化,也对传统史学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若是要进一步深入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必须要在建立在坚实的断代史的基础上,否则史学史研究流于表面、套路,显得相当空疏。那么研究顾颉刚史学理论与思想的学者,若是不能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过先秦史、经学、小学等传统学问及学术史,那么研究者很难读懂、理解顾颉刚的著作的含义,不大可能讲清楚顾氏比清代学者及同时代学者的高妙深入之处,亦不可能进一步站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对顾氏的学术作出总结、定位及准确评价,更别提能够体察顾氏文字之中所蕴藏的“弦外之音”以及顾氏内心真诚情感及灵魂深处的幽微。具体而言,当下学者研究顾颉刚史学理论与思想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学术视野总是停留在“古史层累造成说”,不能触及顾氏史学理论思想的其他方面,即使在此范围内,也不过论述“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学术渊源、形成、影响而已。第二,学术方法上,大多数学者拘泥于中国史学史的经典范式,缺乏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第三,研究内容上,研究者关注与探讨的往往是某一历史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观念的变化。[4]第四,研究材料方面,一些研究者不能积极使用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全集》,他们阅读和使用的资料比较零碎,掌握的材料不全面。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往的历史事实会获得人们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同样,历史学家会主动根据新的社会现实、知识体系及思想认识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再研究、理解、阐释。[5]学术界将顾颉刚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者,实始于王明珂,王氏明确地讲到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可有与之同时或略晚的西方实验心理学家与社会学者相继提出的“人类社会记忆”学说之雏形。[6]王氏虽然始言之,但只有学术洞见未见其具体阐发,又学术界呼应者寥寥无几。笔者试承王氏之论而深刻论述、阐发。
当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界在大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之时,亦不可忘本土的优秀传统,当要有“新儒家之旧途径”与“道教之真精神”,这样才能“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7]此亦为笔者作此文章的衷心之一。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史学是对现代西方大写历史的反思与挑战,虽然是西方学者谈论自家之事,但是其反思之角度及内容亦可成为我们重新思考、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扇新窗户甚至是新天地。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叙事是史家建构出来;历史书写背后是权力的操控;史家无法摆脱自身的立场等等。笔者就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强调的(1)历史叙事中的发现与发明,(2)历史书写与权力,(3)历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蕴涵,(4)史家立场与历史编纂,(5)史实、传说与神话五个方面重新阐发顾颉刚的史学理论与思想。
在此必须特别说明,笔者是从顾颉刚的著作中发现顾氏考证、论述背后的理论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多有暗合之处,而非顾氏自道也。然而,诚所谓“中学西学皆为人学”,古今中外的思想本身就有汇通融合之处。历史比较研究需要建立在共时性或者相对意义上的共时性的基础之上,[8]就共时性而言,顾颉刚(1883-1980)的生命时光与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上有二十年的重合期,若是略微放大视野,他们在大的时间段落上都属于20世纪。就内容而言,笔者进行比较的对象都是围绕史学理论与思想展开的,所以从学理上完全可以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对顾颉刚史学理论及思想进行新释。
一、历史叙事中的发现与发明
当下历史学家基本接受及承认如下的历史认识,从单个的历史事件及由单个历史事件累积起来的编年体史书到含有全景式解释的历史叙事式的历史著作,这是由史学家个人来完成的。海登·怀特以为史家是通过情节化设置或运作的过程将纯然的编年炮制出历史故事;从事件到故事的炮制过程中,其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压制或者贬抑其中的某些东西,而突出的另一些东西,通过描画、主题重复、语调和视角的变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9]笔者以为这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讲的史料的取舍与剪裁,在此以章学诚的“独断之学”简要地说明之。章实斋主张成一家之言之学,成家之学重在个人能够“神解精识”(《家书三》),[10]或称为“别识心裁”(《申郑》)、[11]“性灵”(《与周永清论文》)、[12]“独断之学”(《答客问中》),[13]此即章学诚论史学三才之“史识”。史家通过个人的“別识心裁”,做到“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答客问上》),[14]足以将“比次之书”中的一堆堆的史料化成“史学”。腐朽的史料正是历经史家取舍轻重之手而化为神奇的史学,章学诚的“独断之学”及“別识心裁”之说正可与西方史学理论家所讲历史叙事是史家自我建构之说相媲美。
每个史家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情节设置,于是单个的历史事件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众多单个历史事件也就被炮制成不同意义的历史叙事。这样,历史叙事的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发明的”,[15]“历史叙事”就被描绘成了“言辞的虚构”。彭刚将上述怀特的观点概括为:“历史文本中固然有来自史料的、被发现的成分,然而,人们在史料基础上的选择、建构、情节编排、想象、赋予意义等‘发明’的成分,却也是历史文本中不可或缺的。就此而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并无根本分别。”[16]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承认众多典籍所记载的某单一历史事件及由若干单一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历史叙事中是有一个相对真实的原型,而非全都是作者的建构,这是有异于后现代主义史家之处。只是时代愈后的典籍对故事原型改易愈烈,所添加的其它成分也愈多。[17]我们不妨遵循顾颉刚的意见,将古代典籍都看作是记载历史的文本(text),围绕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可以大致按照它们(历史文本)形成年代的先后排列出一个作者1与历史文本1、作者2与历史文本2、作者N与历史文本N的序列,比较晚的作者总是在阅读较早的作者的历史文本再纂写其新的历史文本,既然形成一个新的历史文本,那么新的历史文本必然有区别于原先的文本的部分,然亦有继承的部分,所以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的历史叙事的发现与发明及“历史叙事是史家自我建构说”有相合之处。
从顾氏大量的史学研究明显可以看出,顾氏希望通过对典籍的辨伪、考证等严格的史料审查、批判的途径来求得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史实及历史故事(即历史叙事)。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中最为深切著明的历史叙事有两个大方面:(1)周公东征以后徐及淮夷的迁留,(2)熊族和嬴族(祝融族和鸟夷族)的整个民族的历史的发展演变。在此,以徐的迁留为例来说明顾氏如何利用众多单个的历史事件来重建全景式解释的历史叙事。文献所见徐国的材料总是分散零乱,那么如何将这些“徐”联系起来,并且能够讲成一个具有统一性与融贯性的“徐国迁徙及其兴衰”的历史叙事呢?这不仅是理论家怀特所言“情节化设置”,更关系到史家的史识与考证功夫。文献中所见之徐有鲁东之徐、齐西南之徐、齐北之徐、江汉之徐、泗州大徐城之徐,[18]哪些是徐人原居住地呢?哪些又是族群迁移而带旧地名冠于新地之上的呢?在总体方法上,顾颉刚通过西周历史上如周公东征之类的大事件对徐人造成的影响的方式分析徐国被迫迁徙的缘由及过程。顾氏首先据《费誓》、《閟宫》判断徐的大本营在山东,在整个山东其故地又有鲁东、齐西南、齐北三处;次据《班簋》(《集成》04341)铭文推测在周穆王时期毛伯班“三年静东国”迫使徐国不得不南迁;再据《常武》“濯征徐国,如汉如江”与《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推断其南迁先处于淮汉之间;最后据《常武》与《括地志》推断周宣王时代徐人受到周人压迫而沿淮东行到今安徽泗县。[19]零散甚至有一些记载矛盾的历史文献,经历了被顾颉刚“別识心裁”之后,于是就有了一个“徐国迁徙及其兴衰”的历史叙事。一般史学工作者可能以为这是顾颉刚考证水平高深,但是他们似乎不曾疑问为何同时代甚至偏后的学者没有写出与《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同等水准的历史研究著作呢?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正是顾颉刚个人的“別识心裁”。历史理论专家何兆武曾有如下令人信服的论断,“一个历史学者之理解历史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水平与能力”,“对历史学家而言,看来理论思想的深度或心灵体会的广度要比史料的积累来得重要得多,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20]正是由于诸多遭遇及经历所造就而成的顾颉刚他个人的“別识心裁”、“灵魂能力”才使得他在阅读文献典籍时能够重构出“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的历史叙事,以及在此历史叙事框架之下的“徐和淮夷的迁留”、“祝融族诸国的兴亡”、“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等具体的历史叙事(或可称为历史构图)。
中国古代典籍繁盛,古代学者在阅读理解前代典籍然后再著书立说时,一方面确实能够发现典籍原有的内涵,另一方面更包含他自己的发明,他的发明或是出于某种现实需求或是为原来典籍作解释、辩护、圆场。作为专业历史学研究者,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是探求真实的历史史实,另一方面要探求后来的典籍在发现原有典籍本身内涵之外又是如何发明原有典籍的的内涵,寻求这些作者发明的动机、目的、结果及影响。许多号称将众多单个事件复原出真实历史的历史著作中自然不乏有作者建构的成份,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就曾深刻批判《春秋》三传为《春秋》“梁亡”主观的伪造解释,三传给梁国编造与发明罪行使梁国的灭亡显得有不突兀而有头绪与条理,那么在此以《春秋》及三传记载梁国的灭亡为例说明历史叙事中对史料本身内涵的发明。
《春秋》僖公十九年仅记载“梁亡”二字,顾颉刚认为司马迁据《秦纪》撰写《秦本纪》时对梁国灭亡历程交待地比较清楚,可以补充鲁史的缺佚。[21]《秦本纪》载梁伯、芮伯在秦德公元年、秦成公元年皆来朝,后来秦穆公二十年“灭梁芮”,《六国年表》作十九年,梁国灭亡的年份为鲁僖公十九年,即秦穆公十九年、晋惠公十年。穆公秦国东进争霸必然要灭秦晋之间的梁、芮,梁、芮之灭亡实是地缘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形势下的必然结果,然而《春秋》三传通过解释、编造罪状来构成一个梁国灭亡的历史叙事。顾颉刚批评说:“他们看到梁亡而‘未有伐者’,就释为它自己‘渔烂而亡’,这是《公羊传》的说法。继起的《谷梁传》的作者看到这个说法不太圆满,就替梁君加上许多罪状,一是‘湎于酒’,二是‘淫于色’,这是使他‘心昏,耳目塞’的缘故,三是‘上无正长之治’,这是使得‘大臣背叛,民为盗寇’的缘故。”[22]东方鲁国史官对梁亡的情况了解不多,后来之说经者读书不多而就经说经,硬是活生生地整出来一些欲加之罪。顾颉刚认为这种作法的根本缘由在于:“这部书因为说是‘孔子作’的,读者无条件地信奉它,以为其中必然处处存在着圣人的大义微言,因此要把每一条文字的褒或贬的意义都猜测出来。”[23]古代儒家学者尊圣崇经的心理在暗地发挥作用,使得他们在解释历史时制造了许多想象的诬枉之辞。
二、历史书写与权力
近半个世纪以来谈权力者,最有影响者当属福柯,福柯的权力——知识观的核心就是权力与知识是直接指涉的,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形成的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没有独立权力之外的知识。[24]在此借用王明珂的语言表述来作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我们生活在历史知识构成的社会现实之中,社会现实塑造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与构建,因此,当现实成为一种社会权力支持的正统、典范,与之相应的‘历史’也成为了典范知识”。[25]这些典范与正统千年积淀而渗透进入民众骨子中,但是广大民众是日用而不知。若是个人的认识偶尔地偏离了这个社会现实塑造的知识与认识之外,那么便被打成上了典范与正统之外的“异端”的标签。
权力知识理论应用于史学史领域,常常表现为分析权力是如何塑造、影响历史书写,尤其是那些被权力否定和抹杀而不见于正史中的历史史实。[26]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较早地表达出了史家掌握着历史书写的直接权力而影响着历史书写。《伯夷列传》云“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又云:“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27]许由、务光等人是当时的风流人物,但是司马迁就疑惑、感慨地发问:历史上存在过许由、务光这样道义至高之人,且记载他们事迹的文献也不少,然而后来为何他们被历史遗忘了?相反,孔子所序列的古代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等人却为世人熟知。司马迁并非得意自己掌握书写历史之笔,而是表达自己要坚决记载真实的历史。顾颉刚的著作中常对掌握历史书写权力的周人所记载的历史叙事加以批判,亦常表现出来对受周人压迫与剥削的族群的同情,这是一种在现代平等观念下所从事的史学研究。至于顾氏为何表批判周人书写的历史,表达对殷遗民的同情,这个的问题值得另外继续探究。
周初分封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内容,周公分封伯禽于鲁,使殷民六族职事于鲁,实际他们沦为周人剥削的对象,《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公分封鲁于少皞之虚,对于殷民六族,“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28],这样的历史记载是处在统治地位、掌握权力的周人的历史书写。殷遗民“只有低首俯心,听凭鲁公的驱散了。他们作奴隶的苦痛,却昭显了周公的明德,这真是奴隶主的自高自大的思想”。[29]《左传》的作者哪里会考虑到殷遗民及东方土著的境遇与感触呢?近年虽有新出铜器铭文表明殷遗民在西周地位甚高,但是这仅为小部分上层贵族而已。幸好《诗经》中保存了被剥削者的真实声音,“大东小东,杼柚其空”[30],便可想象广大东方殷遗民及土著所遭受剥削之残酷。“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解释为“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31]于省吾考证出“绥”字古义为以绳索缚系,“士女”均为壮年男女之为奴隶者。[32]顾颉刚指出《孟子》所引:“原是周公东征攸(条)国胜利之后,大抢大掠,捆缚了他们的男女做周人的奴隶,夺取了他们装在筐子里的币帛来给周人享受”。[33]孟子或不晓得原文之本义而误读,若非经过于省吾、顾颉刚的考证与解释,“贡”的剥削就永远被美化为赠送的礼物,殷遗的痛苦反而被美化为对周人到来的欢庆,历史的真实就淹没在周人话语中了。
顾颉刚在论述周公东征后东方民族的迁徙中,时常直接表达对压迫剥削弱小民族的周人的批判、愤恨。周人对其他民族的剥削形式主要有贡与事,贡多为进贡物品如布帛原材料等,事为摊派的各种劳役。[34]《兮甲盘》(《集成》10174)铭文表明淮夷长期为周人进贡布帛、积谷、奴隶,宣王时期淮夷极力反周,顾颉刚分析南淮夷反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周王朝定下的所有属国对于它应负的大量职贡物品的制度超过了各国所能负担的限度;所谓‘成周四方𧵩’就是极其残酷的经济压迫的政策。”[35]《鲁颂·泮水》“大赂南金”,《仲偁父鼎》(《集成》02734)“俘金,用作宝鼎”,《晋姜鼎》(《集成》02826)“俾贯通,征繁阳,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曾伯簠》(《集成》04632)“抑燮繁阳,金导锡行”,这些铭文都是周人自我赞赏与夸耀的文字,但是周人视此般掠夺为正当行为而没有丝毫内疚感,顾颉刚批判这些文字“都是赤裸裸地把战争的目的招认出来的罪状,在这样无休止的掠夺下,哪得不激起对方的坚决反抗”。[36]《禹鼎》(《集成》02833)铭文记载宣王的父亲厉王命令西六𠂤与殷八𠂤进攻鄂侯要做到“勿遗寿幼”,这或许是早期历史中战争的常态,但顾颉刚特意评论:“周王的‘勿遗寿幼’一语,是要把敌方的老年、少年一网打尽,态度何等凶恶。”[37]显然顾氏是要特意揭露过去一直被高度吹捧赞扬的周王朝及其统治者不为后人所知的另一个凶残黑暗的面貌。
顾颉刚在论述周公东征后东方民族的迁徙中,情不自禁地对这些弱小民族的遭际表达出同情、哀怜。如对春秋时期衰亡的徐国表达了“竟然成为楚王手中任意摆布的玩物,没有一点自由”[38]的无奈与同情。又如对没有被周人迁走的任、宿、须句、颛臾风姓四国的境遇发出“自入春秋时代都已奄奄一息,到了由人家宰割的程度”[39]愤怒、悲哀之情。传统史书及史学哪里会对弱小者抱有同情呢?注意到边缘人群、弱势群体以及默默无声的群体正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兴起之后才将他们纳入研究者的学术视角之中的。自此而言,顾颉刚对周人剥削与压榨的批判及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怜悯确实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书写的背后是权力及注意边缘弱势群体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历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蕴涵
许多史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与影响,怀特在《元史学》中对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系列规定,它使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范围内采取一种立场并遵照执行;伴随着这些规定的是,它们都声称具有‘科学’或‘现实’的权威性。”[40]怀特所列举的意识形态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显然,这几个词汇的适用范围存在局限,笔者以为存在于中国古代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严守君臣之防。
周公称王之事自《尚书·周书》、《荀子》等书皆可明之,然《周书》深奥难解,《荀子》在古代处于儒家经典的边缘位置,古代经师基本否认周公称王。西汉今文经学为政治所利用,王莽利用周公居摄践阼的故事篡汉失败后,最高统治者为防止权臣篡位情况的出现而对周公称王之事就具有极大的警惕。郑玄注《尚书》,一方面注《大诰》“王若曰”为周公摄政时的讲话,一方面注《康诰》“王若曰”为周公代成王发布诰命。今本《书序》亦是将周公东征的诸多事情变成了成王与周公共同出征之事,顾颉刚指出:“今本《书序》里所以只见成王的威风而周公平凡化了,这便是作伪古文尚书的人卫护皇权的苦心孤诣的表现,是有它的一定政治性和时代性的。”[41]
《康诰》中“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一语,[42]古代学者讨论纷繁,清代著名史学家崔述认为《康诰》是武王封康叔为卫侯,诰康叔之辞。[43]崔氏将王告诫康叔与封康叔于卫视为同时之事,皆在武王时期。但是清代著名经学家雷学淇却主张:“《康诰》作于康叔为司寇之时,在武王之世,此时是自畿内之康徙封卫也,故《康诰》一篇皆武王告康叔慎罚之辞。”[44]雷氏活生生地将康叔封卫这一历史事实强行划分为《康诰》为武王告诫康叔与《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所言以殷民七族封康叔于卫两件独立的事情。但是自周初历史形势及《康诰》原文来看,明显可见“王若曰”的“王”只能是康叔之同辈,又分封康叔于卫这一事件的发生必须是在周公平叛武庚及三监之乱之后,故《康诰》“王若曰”的“王”就只能是周公所为。顾颉刚认为:“这就是为了‘君臣大义’给宋儒宣传得愈来愈深彻猛烈,他们在伦理观念上已绝不容许大圣的周公有称王的悖乱行为,所以必要把《康诰》里称康叔为‘弟’的‘王若曰’送给武王,而和周公解除关系。” [45]这便是维护君权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必然认为周公是不会称王的。
近人王国维从古彝器铭识来证明古诸侯称王,[46]杨树达据铜器铭文从铭文直接证明周公称王,[47]丁山据《六月》说明抗击猃狁之主帅尹吉甫也被唤作王,顾颉刚结合人类学、民族学材料从世界早期历史的共通性上来解释周公称王,[49]眼光更为开阔,格局更加高远。顾颉刚认为:“历代皇帝的心传,惯用高度的压力把臣子的地位压得愈来愈低,而皇帝自己的地位则抬得愈来愈高,这就是所谓‘天泽之分’。而一般封建士大夫为了讨好皇帝以巩固官僚集团的统治,也乐于作出这样的宣传,于是两千年来专制政治成为定型。”[50]正是这个古代大臣必须严格遵守的君臣之间的“天泽之分”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古代经师与儒生不承认周公称王的根本原因。
四、史家立场与历史编纂
史家是史家自身立场的囚徒,自身立场包含史家自身时代、地域、社会群体、性别的陈规、预设或心态等。[51]换句话说史家之立场即其偏见,布迪厄概括三种认知偏见为社会性偏见、学术场域偏见、学术偏见与学究偏见。[52]后现代主义认为古今学者皆难完全自拔于其立场之外,那么,他们自然难以完全摆脱偏见。下文就从具体的几个案例来说明顾颉刚在《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中体察、分析、解读古代学者的学术立场及偏见如何造成他们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犯错误,以及古人处于什么立场、目的来掩盖历史真相,如何杜撰、伪造历史。
司马迁编撰《五帝本纪》依据《尧典》列举虞廷之臣有益无伯翳而有彭祖,编撰《陈杞世家》亦依据《尧典》列举虞廷之臣有益有伯翳,在《陈杞世家》中叙述虞廷中舜、禹、契、后稷、伯翳等人的后代的历史,将秦列为伯翳之后,然而疑问《尧典》中垂、益、夔、龙之后代及封地不知去哪儿了,这显然是分伯翳与益为二人。唐代的司马贞为《陈杞世家》作《索隐》已经指出:“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尧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53]近代古史专家杨宽、顾颉刚皆有专文论益与伯翳为一人之说。[54]司马迁在《陈杞世家》所犯的分益与伯翳为二人的错误尚属小错,更大的错误在将秦之先女修当作颛顼的苗裔孙了。在《秦本纪》中,一方面记载大费佐舜调驯鸟兽而封为伯翳,赐姓为嬴,另一方面记载大费之上为大业,大业之上为女修,女修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故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然而司马迁追溯女修的身世却出了问题,“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55]据《五帝本记》“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56]既然颛顼为黄帝之孙,则秦之祖先通过颛顼这个桥梁也可以远溯至黄帝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原则和立场为“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57]当各种记载发生冲突之时是以儒家六艺为标准而进行判断、考证与抉择的。先秦学术大体可以分为“王官学”与“百家言”两大阶段与类别,“百家言”出自“王官学”,儒家虽属“百家言”,然相较其他诸子所载较为接近“王官学”,故有学者认为儒家为古王官学之宗子,诸子学为古王官学之别子。[58]由此而言,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史学原则确实有其进步性,但是亦暴露出其局限性。唯独《秦本纪》说秦之祖为“帝颛顼之苗裔孙”,顾颉刚批评史迁云:“推想司马迁之所以敢于这么武断,只因为他读《帝系》这篇书太熟,他酷信中国的高级统治阶级全是黄帝、颛顼的子孙;少皥在这篇书里没有取得地位,因此他就大胆地把少皥的子孙嫁接给颛顼了。然而《帝系》这篇书出于楚人之手,所以它所叙的世袭,只限于唐、虞、夏、商、周五代帝王以及陆终氏全族的祖先,暗示人们楚必继周而王,故意不把嬴姓等族收进,这和《世本》的遍记各国世系原有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在。” [59]《帝系》一书的撰写本身具有政治目的而不将少皥族写入,司马迁考信于六艺与过于相信儒家的学术立场,且在古代史上所下功夫较少,故犯下这样的错误,实有损其良史的形象。
《秦本纪》云:“其(中衍)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60]中潏为蜚廉之父,周公东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之父如何能在殷商末年受封西土呢?顾颉刚怀疑:“这如果不是司马迁的错记,就应该是秦人西迁之后,为了掩盖他们被迫移徙的耻辱,进一步表示自己和西戎的历史渊源,是由于夸耀门第的需要而杜撰的故事。”[61]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史官由于某种原因都要为其所在王朝的先祖的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来做掩饰。
《礼记·明堂位》是记载周公称王的重要文献,《明堂位》在记载周初分封鲁国时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62]然而《孟子·告子下》明确地讲战国中期几经扩展的鲁国“方百里者五”,而周初“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63]面对《孟子·告子下》与《礼记·明堂位》存在的明显矛盾与冲突,郑玄注《明堂位》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鲁以四等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积四十九,开方之得七百里。”[64]郑康成可谓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拉出二十四个附庸国来凑七百里之数的方法,却被顾颉刚讥讽为“这真实是一个可笑的附会”。《明堂位》又云:“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弒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65]被顾颉刚评论为“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就是翻阅过《春秋》的小孩都知道是《明堂位》这句话压根是在瞎说。探寻这些错误的文献记载所产生的渊源,顾颉刚总结为:“儒生们死心眼儿厚古薄今,把周公捧到天上,希望周公的制度成为宇宙间永恒的秩序,那就只有得着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的结果而已。”[66]这正是儒生们的崇圣尊经的学术偏见及立场所造成的历史事实上的错误认知。
周公东征之后,据清华简《系年》记载秦人被迫从山东潍水流域商奄迁徙到甘肃甘谷县。[67]据《史记·秦本纪》蜚廉之子季胜的后人造父被周穆王封到赵城,蜚廉之子恶来的儿子女防的后人非子居犬丘。[68]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赵城本是周厉王奔彘之彘县,后来改名为永安,犬丘为雍州始平县。[69]彘县为今山西洪洞县,始平县为今陕西兴平东南十里。《水经·汾水注》言蜚廉善终于山西的霍泰山,[70]并非如《孟子》“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与清华简《系年》“飞廉东逃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廉”所言死在了海滨,[71]顾颉刚敏锐地觉察到:“造父封于赵城,北据霍山不远,因为飞廉是赵的直系祖先,所以赵人就替他装点古迹于霍山,说他独得天佑,寿终在这里,至于恶来则是他们的旁系亲属,就不妨实说他凶死了。”[72]《汾水注》所本之材料可能是赵人的史官记载或赵人的口耳传说,赵人的史官或民众就是出于维护其祖先颜面的立场而窜改历史。
既然秦赵同祖飞廉,赵国的祖先造父被周穆王封在山西的赵城,那么秦在非子及其父大骆之前的秦诸祖的居地可以推测在山西而距赵城不远。[73]周孝王受封于秦,即今甘肃清水县,秦襄公时迁移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文公迁移至陈仓,德公时建都雍城。雍城有雍县、雍水,自《散氏盘》(《集成》10176)“淮𤔲工虎”、《汉志》右扶风“淮水祠”[74]及《水经·渭水注》中的“雍水”今日被呼作“𣲗水”等材料,顾颉刚据之综合论证出“雍”、“淮”是原先居住在潍水流域的秦人从山东带来的地名,并不是当地本身的地名,[75]诚为石破惊天之语。《禹贡》九州有雍州,顾颉刚认为:“为了秦人住在那里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所以《禹贡》的作者就规定从西河到黑水这一区域的名称为‘雍州’。他万万想不到‘雍’即是‘淮’,这个水名和邑名都是周公东征之后原来居于潍水流域的鸟夷族西徙后的新名词,在传说的大禹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76]在顾氏看来,《禹贡》的作者含有感情、目的与立场,为了拉长秦人所居雍城的历史竟然追溯到大禹划分九州之时,这不仅是《禹贡》作者由于匮乏一定历史知识而侧漏出来的无知,更是《禹贡》的作者先前就有目的、立场存于心中。
五、史实、传说与神话
美国汉学家柯文所著《历史三调》一书提出历史包含事件、经历及神话三个层面:史学家解读出历史事件的基本史实,当时亲历者对事件的直观感受、想法,后来在历史事实上构建的诸多神话。[77]自从柯氏书中文版上市,这种论说风靡中国近代史学界,广受好评。其实这种史学思想并非是柯文所独创,顾颉刚相当早地将历史划分为历史事实、传说、神话三个层面。两相比较,仅仅存在“传说”与“经历”之区分而已,当然传说的范畴可以包含经历者对当时发生之事的感受。
传世本《尚书·金滕》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这两句中的“弗辟”与“居东”的含义自汉以来充满争议,“辟”字是训“法”还是训“避”?“居东”之“东”又在何处?为何居东二年罪人就斯得呢?顾颉刚在前人基础上认为《金滕》必不是西周作品,至多只能说是战国人根据了晚近的传说写出来的西周史。笔者以为不能以史学作品的某些史料来源的年代将史著的成书年代提早。顾颉刚云:“在历史事实上,周公只有东征,并未居东,居东乃是由东征转化的传说,而《金滕》写出的则是这个故事的全貌,所以我们不但应从周诰和金文里看出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应从各种文献资料里看出战国、秦、汉间人对于西周初年的史实经过加工改造的传说,这正如我们要从《慈恩三藏法师传》里认识实际的玄奘,但也有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演义》里认识神话、传说中的玄奘一样。”[78]这便是顾氏最为集中的表述他对历史所包含的几个层面的认识的文字。以《金滕》所载“周公居东”为例,从学术史纵向演变而言,清代治古史的著名学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与崔述《丰镐考信录》皆认为周公“居东”之“东”在丰镐附近,[79]实为他们基于相信经书《金滕》记载无误的前提下得出的认识,诚如余英时所言,顾颉刚则是“把古代的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document)来处理”。[80]顾氏相较雷学淇、崔述对这些古代儒生奉为至高无上的经书所记载的内容是持有严格的审查、批判态度。先秦史专家杨宽认为“居东”就是周公兴师东征,王玉哲亦认为周公奔楚、周公居东及周公东征实系指的同一回事。[81]清华简《金滕》云:“周公石(宅)東三年,祸人乃斯得。”[82]李学勤、朱凤瀚据清华简《金滕》认为居东三年正是东征三年之事,杜勇进一步深入论证居东即东征。[84]从新近出土资料来审视周公居东之问题,可见顾颉刚以史实与加工史实转化出的传说来解读是东征与居东的关系确实是了不起的,亦可见中国前辈学者在1980年代之前已有将历史划分为史实、传说与神话的三个层面的历史认识论,诸如此等的史学遗产是应当得到总结、继承与发扬的。
传说之中或有真实的历史事实,如关于徐偃王的文献记载中,《赵世家》、《秦本纪》记载周穆王打败了徐偃王,《韩非子·五蠹》、《淮南子·人间》却分别视徐偃王与楚文王、楚庄王为同时期之人,自《班簋》(《集成》04341)铭文可证《史记》之说正确。[84]顾颉刚推测《史记》相关的史源是赵人冯遂讲给司马谈的故事,司马氏父子将周穆王破徐偃王的故事写入《史记》,“这个故事,本身虽也是一个传说,但却接近历史。”[85]西晋汲冢古墓出土了《穆天子传》,此书中记载了周穆王西巡,徐偃王造反,穆王日驰千里,平定叛乱,但是汉代的司马谈父子并未见过此书,那他们是从何而知呢?顾氏云:“不过这件故事必然在社会上流行,尤其是赵人喜欢夸张他们的祖先调御骏马的能力,一定常常称道在口头,无意中就把伐徐的事和西巡的事结合起来,好像因为穆王的盘桓不归,偃王才乘机起事似的。”[86]
传说当然多有讹变,如有关三监及东方诸侯反周这一军事事件中,成书较晚的《尚书大传》有“奄君蒲姑谓禄父曰”[87]的记载,这显然误解泰山南北两个国名奄与蒲姑为奄国君主名叫蒲姑,顾颉刚断言“这无疑是传说的讹变”,[88]亦可见《尚书大传》的作者的古史知识的低下。
当然,历史事实经过讹变之后形成一个故事或传说,这个故事又不断的演变形成更多的故事或传说,那么研究故事之演变又可进而窥见全部的历史。顾颉刚早年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时就曾言:“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乃是这件故事的如何演变。这个变化的样子就很好看了:有的是因为古代流传下来的话失真而变的,有的是因当代的时势反映而变的,有的是因地方的特有性而变的,有的因人民的想象的变的,有的是因文人学士的特有性而变的,这里边的问题就多不可数,牵涉的是全部的历史了。”[89]若是对照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90]之说,笔者以为顾氏的故事研究可以说是“凡研究一故事的演变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解释一字尚且多承乾嘉经学考据的遗风及吸取20世纪流行的历史语言学之新风,但是研究故事及传说的演变则是历代士大夫所不屑的,实则更具有开创性与前瞻性。
顾颉刚以“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引发了中国史学之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大门。[91]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为《顾颉刚全集》,时人既可以从中直接汲取一代学术宗师的学术成果,亦可以从中体察、学习及研究顾氏的史学理论与思想。顾颉刚的史学理论中最著名的就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相较而言就使得顾氏其他史学理论与思想暗淡了许多,更有待于开发与研究。后现代主义史学总体上认为历史叙事多是由史家建构起来的,这其中包含对原有史料及历史叙事的发现与发明,后来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建构,则又会有不断的发现与发明,如此循环则必然会有一个层累的历史叙事造成说。当下,学者应结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来重新认识、反思及阐发顾颉刚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及其具体史学研究,进而站在前贤的肩膀上推动中国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发展。
【注釋】
[1] 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41页。参阅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收氏著《初识清华简》,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40-144页;王洪军:《新史料的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3] 乔治忠:《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7页。
[4] 参阅近年出版研究顾颉刚史学的专著如黄海烈:《顾颉刚“层累说”与20世纪中国古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李政君:《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5] 参阅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24、26-27页。
[6]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页。
[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2-285页。
[8] 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收入氏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9]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2页下栏。
[11]章学诚撰,叶长青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
[1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86页下栏。
[13]章学诚撰,叶长青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7页。
[14]章学诚撰,叶长青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
[15]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43页。
[16]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第42页。
[17]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1页。
[18]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00-809页。
[19]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12、919、823、828页。
[20]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第24、26页。
[21]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17-1019、1022页。《秦纪》叙事文字过于简约,只会记录灭国,不会记载原因。有关《秦纪》的情况,参阅程平山:《襄公、文公年代事迹考》,《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第166-167页;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广濑熏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1-269页。
[22]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22页。
[23]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20页。
[24]参阅加里·古延:《福柯》,王育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52-56页;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25]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26]参阅米歇尔德·塞尔托:《书写与历史》,《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5页;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37-40页;孙卫国:《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塞尔托的观点比较偏激,然毕竟提供了一种将权力因素融入到影响历史书写过程中的新视角。
[27]《史记》卷61《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1页。
[2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35页上栏b。
[29]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716页。
[30]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88页下栏b。
[31]焦循:《孟子正义》卷12《滕文公章句下》,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67页。
[32]于省吾:《〈夏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6-148页。
[33]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715页。
[34]参阅赵世超:《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上),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收入氏著《中西早期历史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赵世超:《周代国野关系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2-114页。
[35]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41页。
[36]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40页。
[37]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40页。
[38]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13页。
[39]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968页。
[40]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41]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664页。
[42]学者或断句为“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维乃丕显考文王”,见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1-312页。
[43]崔述撰,顾颉刚编订:《丰镐考信录卷之八》,《崔东壁遗书》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447页。
[44]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57页。
[45]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666页。
[46]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2-1153页。
[47]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0-382页。
[48]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1-62页。
[49]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679-681页。
[50]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681页。
[51]彼得·伯克:《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
[5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1-43页;参阅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7页。
[53]《史记》卷35《陈杞世家》,第1916-1917页。
[54]杨宽:《伯益、勾芒与九凤、玄鸟》,《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5-285页;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945-946页;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0-265页。
[55]《史记》卷6《秦本纪》,第223页。
[56]《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4页。
[57]《史记》卷61《伯夷列传》,第2581页。
[58]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页。
[59]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全集》11《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 946页。笔者案:有关《帝系》之分析,参阅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983-989页。
[60]《史记》卷6《秦本纪》,第225页。
[61]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16页。
[62]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24页下栏-3224页上栏。
[63]焦循:《孟子正义》卷25《告子章句下》,第917页。
[64]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25页上栏b。
[65]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32页下栏b。
[66]以上三处均见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647页。
[6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141-142页;李学勤:《谈秦人初居“邾𫊟”的地理位置》,原载《出土文献》第二辑,收入氏著《初识清华简》,第148-152页。
[68]《史记》卷5《秦本纪》,第225页。
[69]《史记》卷5《秦本纪》,第227、228页。《秦本纪》所载孝王使非子“邑之秦”,申侯之女所生之成“为骆之适(嫡)”。《集解》引徐广云:“(秦)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嫡子成居兴平县之犬丘,非子居甘肃清水县之甘谷。
[70]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梳:《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44-545页。
[71]焦循:《孟子正义》卷12《滕文公章句下》,第484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141页。
[72]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12-1013页。
[73]考古学家梁云据毛家坪等考古遗址的年代是西周晚期,考古资料不支持《系年》之说,梁氏极力支持秦人在大骆以前可能就在山西霍泰山附近的临汾盆地,见梁云:《赢秦西迁三说平议》,《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31-41页;梁云:《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9-70页。
[74]《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7页。
[75]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24-1028页。
[76]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1028页。
[77]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3-4页。
[78]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81页。
[79]崔述撰,顾颉刚编订:《丰镐考信录卷之四》,《崔东壁遗书》(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88-291页;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宋志英辑:《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第9册,第252-253页。
[80]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08页。
[81]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3页;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40页。
[8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58页。
[83]李学勤:《清华简〈金滕〉看周初史事》,《初识清华简》,第119页;朱凤瀚:《论清华楚简金縢兼论相关问题》,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8页;杜勇:《清华简〈金滕〉有关历史问题的考论》,《清华简与古史探赜》,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89-293页。
[84]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唐兰全集》第3册《论文集中编(1949-19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62页。
[85]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21页。
[86]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821页。
[87]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22页下栏b。
[88]顾颉刚:《尚书大诰研究·历史部分——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0(下),第689页。
[89]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9页。
[90]陈寅恪说见葛益信、启功编:《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页。
[91]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09-410页。
New studi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Gu Jiegang’s history theories in the horizon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centering on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eastward marching by Duke of zhou
Abstract : The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of Gu Jiegang have many things shared with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By using textual criticism, Gu developed the view of “layer-wise accumulated, fabricate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which is analogous to the theory of the reveal and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Gu’s critiques up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by the Zhou people, and sympathy towards the adherents of Shang dynasty are similar to the idea that all historical writings are about power. Besides, from Gu’s work, we can always figure out those themes emphasized by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such as: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with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ition of historian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composing of history that includes three layers of historical facts, legend and myth.
Keywords : Gu Jiegang,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layer-wise accumulated, fabricated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historical narrative, historical 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