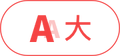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
李新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 元明清以来的皇宫城池,越来越呈现为内外两重结构,但在明代,北京皇城多被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内外两重。本文分析明代两京皇城的建造历程、布局结构、防卫门禁,认为:明代北京皇城,并非按内外双重理念设计建造,而可视为一内城加四瓮城的整体结构。洪武时期的南京皇城,沿南方传统新修内城,为强化防御增建瓮城,后仿元代皇城加筑外城。永乐时期的北京皇城,在元代两重结构基础上,模仿、保留了南京模式,内外城之间瓮城地带的封围、防卫、门禁得到强化,内城与外城的区别相应弱化。所以,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虽较以往更明显地分为内城和外城,在明人心目中却首先是一个内外一体的“皇城”。
【关键词】 明代,北京,皇城,瓮城,南京。
中国古代的皇宫城池,本为环卫宫殿而设,即使城墙由相邻数层构成,亦非内外城之别 [1] 。隋代之前,皇宫城池并不刻意隔绝宫廷、官署与民居,以后多内含官署、外别民居 [2] 。至宋金,大体以宫廷在北、官署在南,虽南北两分,仍非内外两重。元代,内设宫城、外设萧墙,中央行政官署与民居皆在萧墙之外 [3] ,首现比内城大得多的外周垣。明代的北京,内城为宫城即紫禁城,外城为皇城 [4] ,官衙、民居亦在外城之外,近似元代。晋宏逵指出,明初朱元璋受元代影响,建中都、南京的外周垣,“通过设置皇城门官,明确了大内之外的外墙也称皇城,也从此确立了明代大内两重城的格局。” [5] 清代至今,“大内”两重城池的观念深入人心,今人对明代皇宫城池的结构,亦作此观。
但是,明人似乎不太在意这种全新的两重结构。明代常见“皇城”“皇城四门”“皇城内外”,此“皇城”乃对皇宫城池整体的泛称,而刻意专称内城或外城者,明代前中期尚不多见。王剑英概括,明初营建南京、中都、北京宫阙时,专称内城为皇城,但外墙即禁垣包括在“皇城”范围内 [6] 。按,若“皇城”专指内城,就不包括外垣,若包括外垣,就不可能专指内城,两种指称不应在同一语境互见。事实上,明代以“皇城”专指内城者极少。李燮平指出,明初外周垣确立后,原专指内城的“皇城”范围扩大,遂与外周垣统称“皇城” [7] 。常欣指出:“自外禁垣出现以后,宫城和外禁垣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8] 的确,明代前期提及皇宫城池,并无特称外城墙或内外墙之间地带为皇城者。在时人心目中,皇宫城池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皇城”。
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是在元代基址上修建的,而元大都的皇宫城池初见双重规模。元末,陶宗仪载:
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三十五尺,砖甃……东曰东华,七间,三门,(东西)〔南北〕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华,制度如东华。北曰厚载,五间,一门,东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华……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 [9]
元代多以“宫城”指内城,“外周垣”或萧墙指外城。明初萧洵参观北平故宫,称“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 [10] 。官方度量内城,称:“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十六丈。” [11] 以上皆强调“大内”范围内又有一个内城。不过,内外城崇卑悬绝,似难等量齐观。内城城墙与城门规格较高,按元尺合今34.8厘米 [12] ,内城城墙高逾12米,城楼高近28米。而外周垣不称“城”,所设红门多达十五处,与内苑、御苑之门皆称红门,当无城楼,规格远低于内城诸门。其中有“东二红门”“北红门” [13] ,仅以编号、方位命名,可以想见其“寒酸”。杨宽指出,元代内外城之间,并无主管行政的中央官署,萧墙围起东西两个宫殿群和苑囿,只是为加强保卫而增建的大内外围墙垣,称“红门阑马墙”,墙垣比宫城要矮得多 [14] 。如此,元代的内外两重观念,粗具而已。
明代前期,外城沿袭了元代萧墙之名 [15] 。万历《大明会典》载北京内城规格:
城高三丈,垛口四尺五寸五分,基厚二丈五尺,顶收二丈一尺二寸五分。 [16]
按明营造尺合今31.78厘米 [17] 计,则北京内城不计城垛高9.5米,厚达8米,顶部宽6.8米以容守卫。嘉庆会典载明代外城规格:
皇城……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甃以砖,涂以朱,覆以黄琉璃瓦。 [18]
姑以清营造尺合今32厘米米计,高5.8米,厚仅2.1米,顶宽1.7米,与内城相去甚远。另外,晋宏逵据清代地安门、大清门形制指出,明代东安门、西安门为木构屋宇式,七间三开门,大明门、长安左、右门则是砖石构屋宇式,三开门,皆单檐歇山顶 [19] 。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东、西华门的重檐高楼相提并论。
元明的两重城墙,皆内崇外卑。内城是一座标准的高大城池,外城更像一堵附属内城的外墙,似不足以独立身份与内城并列。时人以外墙为皇宫城池边界,而无需强调内外两重的结构。不过,明代的内城,不如元代那样高大,外城则应该比“阑马墙”壮观些,内外城的规格差距缩小了。由此,外城地位理应上升,内外两重的观念,应较元代浓厚,而与清代以来相似。但从明初开始,时人强调内外一体的“皇城”,反而淡化了内外两重。则明代皇宫城池的结构,是否本质上有别于元代,而致明人本无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
一、南京瓮城结构
明朝永乐时期建北京皇宫城池,皆仿南京。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系统介绍南京的皇宫城池,罗列诸门:
奉天门、东角门、西角门、中左门、中右门、后门、后右门、左顺门、右顺门、武英门、文华门、春和门。
午门、左掖门、右掖门、左阙门、右阙门、社街门、庙街门、端门、承天门、阙左门、社右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洪武门。
东华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东安门。
西华门、西中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西安门。
玄武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北安门、亲蚕之门。
以上皆宫门。 [20]
与陶宗仪、萧洵强调内城不同,“以上皆宫门”,既不区分内外,也不分别轻重。第一段可视为,以御门听政的奉天门为中心,介绍内城之内的奉天门前后左右各门,也可视为,以三大殿为核心,先介绍所在院落各门,再介绍内城其他门,总之,皆内城之内各门。下面四段,乃按南东西北,分列各方向的内、外城门。每个方向,从内城门向外,一直说到顶端的外城门为止。内外之分,让位于方位之别。
《洪武京城图志》附图 [21] ,画出内外城墙,但外墙不突出,倒是四个方向的内外诸门,各围绕内外之间的甬道,构成封闭空间。如从西华门到西安门,甬道上有二门,甬道南北有四个门,八门联属,围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瓮城。这种形制,在明清皇宫城池的南门方向,一直存在,即从午门经端门到承天门,两侧围以高墙、开门出入的封闭空间。但是,四个方向皆如此,就从总体上改变了皇宫城池的进出模式:内城经这四个瓮城,通达外城之外和外城之内的地带,而非经内、外两重城门出“皇城”。这是元代乃至历代皇宫城池所未见的新现象。元代内外城之间,并无甬道诸门,四四方方的高大内城,自与萧墙区分内外。但明初的整体结构,与其说是内外两重,不如说是内城配四大瓮城的模式,外城墙被彻底“边缘化”了。
《洪武京城图志》所绘东西两个瓮城,城楼规格、城门设置不同,其中西部道北三门、道南一门。这不一定精准刻画东西差异,而可能是刻意展现建筑形制的灵活可能性。则东西两侧诸门,真会如图中所示,联建高墙,与甬道诸门合围成严格封闭的空间吗?晋宏逵指出,南京皇宫城池内外门之间为“封闭大道”,将外城分为“六大空间”,各区之间经封闭大道的侧门联通 [22] ,尚未明言墙垣之有无,与侧门之规格。按,万历前期,南京光禄寺卿王樵载:
出光禄署,入西上门,循皇城而南,入阙右門,会于吏科……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与御用监相对。御用监,旧丞相府也。尚膳监之左为大烹门,门之内为凉楼……之后为光禄寺。 [23]
南京光禄寺在皇宫城池的位置,与北京不同,位于“内城西” [24] ,即外城以内地带的西部。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东为光禄寺,南为御用监即“旧丞相府”,即洪武初年的中书省旧址。比王樵稍早时,王世贞参观旧丞相府,进外城西门后:
数百步,更入重门,又百余武,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中涓指谓余,此故丞相府也……已而有堂,巍然南向,由堂背以入 [25]
则旧丞相府在甬道南侧,尚膳监在甬道北侧,光禄寺在东北。《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1513),“雷击南京光禄寺大烹门凉楼。”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劾奏尚膳监太监任宣,于南京西上北门乘轿张盖,骄纵无上。” [26] 王樵所记大烹门,应即《洪武京城图志》所示道北东北门。道北正中者,当为尚膳监对应的西上北门。旧丞相府内的建筑都是南向,需要“由堂背入”,则其北门,非原府第后门,应为《洪武京城图志》所示道南之门,即西上南门。西上南门巍峨“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出入西上北门有舆轿之禁,则二门非仅牌楼之类,规格当不低于西中门、西上门等。
洪武十年(1377),明朝“置皇城门官,端门……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 [27] 此守门内官之设,重在申明门禁,各方皆含安、上、南、北四门,而无中门。洪武十八年(1385),“置午门……西上门、西中门、西安门……门吏,各四名。” [28] 此门吏之设,重在处理事务,各方皆含安、中、上三门,而无南北门。则诸上南、上北门,人员往来之频繁或不如甬道诸门,门禁之重则同瓮城东西两端之门,尚在瓮城内部的中门之上。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一伙儿小偷夜间“进西安门、西上门,由阙右门过阙左门,至走更桥下乾水洞内,扒进紫城内东宫殿上”。为此,把守西安门、西上门、阙左、右门的官员皆遭参劾 [29] 。入西上门至阙右门,路线同上引王樵所行。若西上南、北门可通南北,乃至甬道四面未封闭,小偷们完全可以穿行绕至阙右门,不必铤而走险潜过有军队把守的西上门。
由此,西上南、北门并非路口地标,而是正规的大门,临甬道两侧而建,外通明初中书省、光禄寺等,与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各门位置均衡的瓮城,联通内外城。东方、北方,规制亦应类此,与内城南方从午门到承天门的形制、规模相似。
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非按规划一次性建成。吴元年(1367),建成“皇城”即内城。至洪武六年(1373)建成中都后,开始修筑南京“内城”即皇宫城池的外城。洪武十年(1377)底,如上引,设西安门等门官 [30] 。这是西安等门首见记录。则诸瓮城,是否洪武六年(1373)至十年(1377)间,在建外城过程中设置的呢?
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明朝在凤阳营中都,所建皇宫城池,设内城与外周垣。但是,无论历代记载,还是现存遗址,皆无内外城之间诸门和瓮城的任何痕迹,甚至连午门以南的瓮城也不见遗存 [31] 。换言之,中都皇宫城池,有外墙而无内外间瓮城。这与此前刚刚建成的南京“皇城”,适成对比。按,中都开工之初的洪武二年(1369)底,“张耀……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 [32] 中都有外墙无瓮城,与元代一致,当属朱元璋见识元大都之制后所定。此后南京皇宫城池增建的外城,必承元大都、明中都之制。南京增建外城,只言“修筑……内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 [33] ,未言其他。则异于中都之制的瓮城,似非此时增建。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置洪武门千户所” [34] 。皇城的南端,晚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尚名“广敬门” [35] ,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名“洪武门”,而洪武末年、建文、永乐初年,或称“正前门”“辂门” [36] 。这条记载,或系建文、永乐修纂《实录》时未遑还原旧名。但洪武门也并非建文、永乐定名,所以,本条记载完全可能了体现原名与实事。洪武门是外城向南伸出的瓮城南端的城门,而此时尚无外城。若曰内城建成之初,南方已不但建成从午门到承天门的瓮城,而且建成从承天门到洪武门的“瓮城之瓮城”,实难想象。不过,梁庆华等将洪武六年(1373)外城周长换算为8288米,因此时尚未拓展外城西墙,将西部宽度按东部计,再将南方瓮城直至洪武门计算在内,结果恰合实测 [37] 。而明朝官方测量北京皇宫城池周长时,也确实是计长方形城池加瓮城的 [38] 。可见,洪武六年(1373)的外城数据,已将以洪武门为顶端的瓮城计算在内。退一步想,就算这个数据是工程结束后增补的,就算“洪武门千户所”只是在后称洪武门的地方设置了千户所,这个地点应已为重要地标。端门、承天门等南部重门,重要性远超洪武门,虽然洪武十年(1377)方首见《实录》,此前必有设置。
由此,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建内城时,同时建内城南到承天门的瓮城,增建外城时,同时建外城南到洪武门的外瓮城,和内城到外城的其他三方瓮城。但是,若初建内城时,其他三方不设瓮城,似过于单薄。明初的南京城,城墙之高、城门之固,可称空前绝后。今存南京城的南门,内设三层瓮城,主城门厚逾50米,可以想见,明初对门禁守卫之追求,已近病态。与京城相比,皇宫城池防卫之严,必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元年(1367)所建内城,当既非仅简单的长方形城池,也非仅仅在南部伸出狭长的瓮城以壮观瞻。四面瓮城,当早在吴元年(1367)初建皇城、未见元大都规制时,为强化防御而建。后来模仿元大都外周垣,以各瓮城顶端为枢纽,向两侧延伸增筑了一道外墙。总之,南京皇宫城池,看似一个以四面瓮城联通内外两重城墙的格局,实则一个内城加四大瓮城、附加外墙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非继承前代,亦非出自规划,而是明初内城加瓮城的特殊格局受元制启发增补的。洪武建文时期,时人视皇宫城池,当无内外两重观念。
二、北京瓮城遗制
永乐建北京,体制一依南京。但北京的皇宫城池,无需重复先建内城与瓮城、后建外城的过程,当按南京已有的四面瓮城联通内外两重城墙,直接建设。然则,北京是否有四面瓮城之设呢?皇宫城池南部,设两重瓮城。内从午门经端门到承天门,与两侧的阙门、庙社门、街门,构成联通内外城的瓮城。外从承天门到大明门,与两侧的长安门,构成伸出外城的瓮城。此尽人皆知,与南京完全相同。其他三面,似乎没有南京那样明显的联通内外城门的瓮城。但明代前期,皇宫城池虽然是按两重格局建设的,却未淡化“皇城”整体观念,则南京的瓮城结构及其整体观念,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到了北京。
(一)东部封闭空间
据《北京历史地图集》,东、西华门外未设瓮城。而《洪武京城图志》东西部瓮城的规模气势,在北部之上,直追南部。则北京东、西华门外,是否有瓮城遗迹呢?
东华门与东安门,东西相对,距离最短,似宜建成瓮城。但甬道两侧东上南北门的方位,似非瓮城所应有。朱偰据刘若愚详载道路建筑判断,东上南门、东上北门,远在垂直于东华门至东安门甬道的便道南北段中部,西部规制略同 [39] 。《北京历史地图集》标“东上中门”于东华门外的道路交叉口,东上南、北门在南北道路稍近处,诸门无辅墙,仅标识通衢,西部略同 [40] 。按,朱偰仅粗略估计,而刘若愚《酌中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不载东上门、西上门所在,《北京历史地图集》或因此合“上门”“中门”而称某“上中门”。其实,明代记载中,东西上门、中门常见,却无“东上中门”“西上中门”名目。
晋宏逵据外城北部规制、清代地图、西华门外明代地基遗址等指出,明代习惯在主门前布置左右辅门,东、西华门外紧邻护城河设上门,跨门外南北便道建左右门,“左右门与上门距离不会太远”,“明代皇城门、三组中门、上门及其左右门、宫城门的四层组合,是宫门前大道的设置模式。其左右两侧,南门利用庑房,其余三门利用沿街衙署及其围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 [41] 这项推断,严格区分东上门与东上南、北门的东西方位差异,精准合理,但仍以东、上南北门在离开甬道的南北便道上。若然,两门在甬道两侧各凸出一片,与甬道围成一个T字形空间,与南部的长安左、右门与大明门构成T字型瓮城相似,又与北上东、西门即远在东西两侧呼应。但是,长安左、右门在外城之外,而内城东、西华门之外,应更类似内城午门之外。午门之外的阙左、右门,实接阙楼而临甬道,并不向两侧凸出。北上东、西门,乃因万岁山阻隔而向两侧推移,皆位于东西道路和南北道路交汇处。无论将两条南北道路视为被万岁山“绿化带”隔开的一条正北方甬道,还是将万岁山地带视为比两侧南北道路更重要的禁地甬道,二门仍可视为紧临北上门外十字路口而建,未向两侧凸出。
崇祯年间,刘若愚《酌中志》介绍皇城内各衙门、建筑的职能与分布,内容系统、详尽而精确,就明代皇城而言,史料价值在《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之上。此前研究者多有征引,但或与其他史料等量齐观,或因刘氏独特的描述方式和叙事顺序,偶有误读或疏略。刘若愚于东华门外地带载:
东河边……过东上北门、东中门,街北则弹子房……再东则东安里门……过桥则东安门也。
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
自东上南门迤南,街东曰永泰门,门内街北则重华宫之前门也。 [42]
早在景泰元年(1450),明英宗归国,礼部定仪:“太上皇帝……进东安门,于东上北门南面坐,皇帝出见……自东上南门入南城。” [43] 按计划,明英宗要沿甬道至东上门前,再向南拐进南内,拐弯前接见皇帝和百官。礼部似不可能将行礼时的御座,设置在离开甬道的南北便道上,即东上北门当紧邻东西甬道。其实,刘若愚此前先介绍北河沿即南北道路北段沿线,然后介绍东西甬道“街北”。其“过东上北门、东中门”是在甬道上看“街北”,东上北门应该临街即东西甬道。同理,“东上南门之东”是看东西甬道的街南,然后“东上南门迤南”是看南北便道南段的“街东”,东上南门应临十字路口。所以,东上南、北门,实距东上门非常“不远”,正是在东西甬道上临街而建,门后辟为南北便道。东华门经东上门、东中门、东安里门至东安门,与两侧的东上南、北门,构成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封闭空间,与南京如出一辙。
(二)西部封闭空间
内外城之间,西部最宽敞。西北的西安门与东南的西华门相去甚远,长长的道路在内城西北角外的乾明门拐弯,向西经棂星门至西安门,向南直达西华门。《北京历史地图集》将乾明门至棂星门一段,标为南北临湖、四面围墙的封闭小城,将西安门至棂星门、乾明门至西华门两段,标为开放街道 [44] 。按,刘若愚载:
乾明门……由玉河桥、玉熙宫迤西,曰棂星门,迤北曰羊房夹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内安乐堂在焉。棂星门迤西,曰西酒房……曰洗帛处、果园厂,曰西安里门,曰甲字等十库……正西则西安门也。棂星门迤西街南,赃罚别库之门也。门之东迤南,曰蚕池,曰阳德门,又西曰迎和门,则万寿宫之门也,曰大光明殿。自阳德门外,皆可以至河。 [45]
“门之东迤南”之门,当指赃罚别库之门,蚕池位于棂星门西南 [46] 。刘若愚乃以棂星门为起点,依次述其西北、正西、西南。紧邻棂星门的街北羊房夹道,必是垂直于甬道的南北便道。此后向西诸署联比,直达西安门,街南强调为赃罚别库之门临街,皆未提及街道出口。阳德门位于棂星门西南,应即蚕池周边某门,“又西”的迎和门,皆在棂星门西南再向西,在甬道以南较远处万寿宫墙上。万寿宫是嘉靖年间重建的西内,明世宗载:“文皇帝旧宫之迎和门……外之南,作一亭……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 [47] 则迎和门必非北向甬道开门。夏言有诗词“迎和门外柳堤平”“迎和门外日初晴”。 [48] 严嵩载:“于金海边乘凉,是日出迎和门,登舟。” [49] 明末清初人记迎和门牌匾,称“东迎和门” [50] 。可知迎和门乃面对太液池,向东开门。作为“万寿宫之门”,迎和门必临大道,这只能是棂星门以西向南的便道,与羊房夹道南北贯通。总之,从西安门至乾明门的长长甬道,仅在棂星门西向南北两侧开便道,形成十字路口,虽未设门,形制与东华门外的甬道相似 [51] 。
刘若愚又载:
乾明门,门里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曰旧监库……曰尚膳外监,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门。
自西上北门过西上南门,向东,则御用监也。又南向西,则银作局也。 [52]
刘若愚乃自乾明门南对便道,依次介绍道西、便道和道东。其中,由北向南罗列道西建筑,至甜食房,已在东华门至西苑门甬道非街北 [53] 。则甜食房下的最后一处“西上北门”,必在南北便道北段的南端。
朱偰据“向东则御用监也”,许冰彬据御用监在西华门西南一里左右等,认为御用监在南北道路南段之东 [54] 。《北京历史地图集》则将御用监标在道西的宽阔区域 [55] 。按,便道东至护城河,仅50米左右,不足以容纳御用监这样庞大的机构,也不合一里左右。刘若愚言“向”某方位,一般指“面向”,而非“走向”。如介绍南北向的西一长街沿线诸门:“再北向东,与凤彩门斜对者,曰咸和右门……咸和右门之北向东,与隆福门相对者,曰广和右门……广和门〔之北〕向东,与端则门相对者,曰大成右门。” [56] 咸和右门、广和右门、大成右门,皆位于街西,南北相望、坐西朝东 [57] 。所以,“向东则御用监”,不是指道东,而是指御用监大门向东开,位于道西,《北京历史地图集》确。由此,御用监是从北向南“过西上南门”后,看到大门东开的第一个地标,西上南门必在南北便道南段的北端。
总之,西上南门、西上北门,也是临甬道而建,与甬道上的西华门、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构成一个紧凑的长方形区域。刘若愚介绍东、西华门外甬道大街两侧,除上南、北门两侧的便道,从未介绍有其他街道交汇。这两个地段,如晋宏逵所言“利用沿街衙署及其围墙”,形成了不但形状规整、而且彻底封闭的空间。乾明门至棂星门的小城以西,直到西安门,途中仅与一条南北便道交汇,不妨也视为棂星门外相对封闭的规整长方形空间。
(三)北部瓮城与封闭空间
据《北京历史地图集》,外城北部,有两个南北串联的瓮城。偏南者,从玄武门外的北上门至万岁门,与两侧的北上东、西门,构成一个东西很宽、南北很窄的小瓮城。偏北者,从万岁门北过万岁山至北中门,与两侧的山左、右里门,构成一个环绕万岁山的大瓮城。两者叠加,内与玄武门隔河相望,外以大道通北安门 [58] 。此包山而城、北端不接外城,异于南京联通外城的北部瓮城。按,刘若愚载:
皇城内,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北安门内街西曰安乐堂……再南黄瓦西门之里,则内官监也。过北中门,迤西则白石桥、万法殿等处,至大高玄殿……北中门之南,曰寿皇殿。 [59]
“过北中门”向西,为外城西北诸建筑,则北中门必非万岁山瓮城的北门。《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四年(1429),“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昨夜一更初,府军后(军)〔卫〕指挥李春进题本,臣递至北中门,守卫官不肯传达。’” [60] 晋宏逵据此指出,北中门有门禁功能,应横跨北安门内南北道路,可能位于雁翅楼北端 [61] 。按,刘若愚未提及雁翅楼,“过北中门”即介绍“迤西”“之南”,则北中门更可能如单士元推测,在“今地安门大街南端丁字路口处” [62] 。如此,北安门内整条街道,与北中门、街两侧的黄瓦东、西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的空间。
刘若愚言“北中门之南”为宫殿,当指诸宫殿方位,并非指可从北中门径直走到寿皇殿。万岁山以北,宫殿邃密,瓮城北墙似未开后门。万历《大明会典》载,公主出殡,“由东上南门、东上北门、北中门、北安门出。” [63] 灵柩并未经北上东门、北上门进入两个瓮城,而是沿瓮城墙外道路至北中门。可见万岁山周边瓮城,非供南北通行,而是一个交通障碍。出北上门后,需折经北上东、西门,再往北,绕过万岁山,方可汇聚到西中门。如果将万岁山视为南北甬道中央的一条宽阔“绿化带”,则北上门至北中门,也是一个上门之外两侧开门、门后设垂直便道的封闭空间。
晋宏逵据乾隆《京城全图》指出,在内城以北,“从景山东西苑墙延伸出来的围墙一直要抵到护城河边,墙中央辟北上东门及北上西门。从北上门两侧伸出的围墙,‘撞’在东西围墙上,形成神武门外、北上门内的一个长方形封闭院落。” [64] 这不是清代后期的样式,完全可能是明代遗制。明代北上东、西门之南的围墙,除了向内折形成扁平瓮城,还继续向南直抵护城河。这“堵上”了西上门侧后的缺口,构成了从玄武门向外直到万岁山北的瓮城。
可见,城池规划的本意,是构筑从玄武门直抵北安门、联通内外城的完整瓮城,只因万岁山的阻隔,才分为南部宽扁的瓮城和北部狭长的封闭空间两段。这两段区域,内部联以万岁山三侧的便道,外部通向北上东、西门外的便道。其原型及职能,正同东、西华门之外。
上述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外与西安门、北安门内,两侧皆仅设一条垂直便道开口,余似皆为诸衙署围墙,形成严丝合缝的封闭空间。内外城门之间,设中门,将甬道分为两段。内城门至中门一段,两侧开门设道,自属合理。而中门至外城门的一段,似亦应两侧开门,方令中门之设,不至多此一举。北安门至北中门两侧,即设黄瓦东、西门。若拟端门为南部的中门,则其内两侧设阙门等,外两侧设街门等。由此,棂星门可视为西安门内的中门,门外两侧设便道,与北安门内相似。至于东安里门外的南北河沿,必可通行,但这是宣德年间拓展东墙遗留的空白地带,并非规划设置的便道。刘若愚述西安里门,与诸衙署混杂,或因西段道路过长,而仿东安门内设一里门,但垂直便道并无明据。要之,里门皆特例,非关形制。观刘若愚所述,东中门至东安里门、西中门至西苑门,距离甚短,应无其他道路出口。
总之,北京皇宫城池内外城门之外的甬道,皆尽量围成规整、封闭的空间。其中,南部沿袭南京的瓮城规制,北部有万岁山阻隔,建有南段瓮城和北段封闭空间,西部内外城门相去辽远,围成外城门内和内城门外两段,东部内外城之间则严密规整。这个格局,颇见南京四瓮城之意。
三、守卫与门禁
这些封闭空间,貌似瓮城,却不一定具备瓮城的防卫功能。南京的皇宫城池,是先建瓮城以临外部、后增外城,防卫必重瓮城。而在北京,内城、外城包括内外城之间诸门同时兴建,皇宫城池的守卫任务,是按内城加瓮城,而非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布置的吗?这些地带的门禁,比外城其他地区要严格吗?若然,则北京的皇宫城池,确有南京瓮城体制的痕迹。
(一)瓮城式防区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八年(1420),行在兵部尚书方宾提议:
守卫官军旧有定数,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左右门,俱系金吾、旗手、府军、虎贲宿卫。今因别有选调,其数不足,宜増羽林、济川、济阳、燕山四卫军士,相参宿直。 [65]
从午门到长安左右门,既非内城一部,亦非外城一部,而是皇宫城池南部的瓮城甬道地带。与正德《大明会典》 [66] 比对,此八卫全称当为:金吾前卫、旗手卫、府军卫、虎贲左卫、羽林前卫、济川卫、济阳卫、燕山前卫。其中,金吾前等四卫,皆属洪武时旧设上十二卫 [67] ,羽林前等四卫,皆属靖难成功后新设的十个上直卫 [68] 。此时系迁都伊始,金吾前等四卫守卫南部瓮城的模式,当属南京旧制。《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1425),明朝调整皇宫城池守卫:
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一时权益,非为定制。 [69]
“专守皇城四门”,似指守卫分为内重外轻的两个系统,内城四门仍全由亲军把守,外围各门向一般京卫开放。若然,这可能是明代前期以“皇城”专指内城、区分内外城的孤例。常欣认为,这虽属权宜之计,仍反映“宫城与外禁垣之间守卫特点的不同……显露了内外皇城划分的早期痕迹” [70] 。按,“皇城四门”并未明言特指内城四门,助守也未明言包括“承天”“东安”等外城门,况且明朝也不会将承天门托付给关系疏远的京卫军。则助守,更可能指京卫参与守卫内外门间的次要诸门,而非与亲军卫明分内外。明初以来的完整“定制”,最早见于成化年间叶盛抄录的正统十三年(1448)原始文件:
卫士守宿内门,前班官旗军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员名,后班少十名:东中门七、玄武门一、北安门二。
官军三日一点……羽林前、金吾前……大兴左等二十一卫,各具官军等项数目,奏本送科。
午门至长安左右门:午门,阙左门并守铺,阙右门并守铺,端门,承天门,长安左门并守铺,长安右门并守铺。
东华门至东安门:东华门并守铺,东上门并东上南、北门,东中门,东安墙门,东安门并守铺。
西华门至西安门:西华门并守铺,西上门并西上南、北门,西中门,乾明门,西安里门,西安门并守铺。
玄武门至北安门:玄武门并守铺,北上门并北上东、西门,北中门,北安门并守铺。 [71]
守铺,指城墙外设诸巡逻铺,由军人巡夜。某门并守铺的职责,当包括防卫本段城墙。在第一句,东中门、北安门这些外城门,与玄武门这样的内城门一视同仁。在第二句,“二十一卫”就是二十二亲军卫减去职能特殊的锦衣卫、府军前卫 [72] 。在后四句,并未按内外城分别轻重亲疏,而是按四个方向,各从内城门到外城门构成一个单元。这与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京城图志》介绍南京内外诸门的方式 [73] ,高度吻合。每个方向内部,如向东,由内而外,从“东华门并守铺”即内城东墙,到内外城之间诸门,再到“东安门并守铺”,除去外围的守铺任务,即略见瓮城守卫系统的框架。可以想见,洪熙元年(1425)一度增派的普通京卫军,是先分派到四个大单元,在单元内部增添到外围某处。所谓“专守皇城四门”,并未视内城为自成一体的防卫单元,而是指四个方向的瓮城系统,每个防卫系统以“并守铺”的内、外城门为核心。
正德《大明会典》对内、外城门在防卫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介绍尤详:
计各卫分定地方,皇城四门:
自午门左至阙左门、东第五铺,午门右至阙右门、西第五铺。端门左至承天门左桥南,端门右至承天门右桥南。长安左门至外皇城以东第六铺,长安右门至外皇城以西第十一铺。右旗手、济阳、济州、府军、虎贲左、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卫官军分守。
东华门左尽左第十一铺、东至东上门左,东华门右尽右第一铺、东至东上门右。东安门左外尽左第十四铺、内至东上南北门左,东安门右外尽右第十四铺、内至东上南北门右。以上该金吾左、羽林左、府军左、燕山左四卫官军分守。
西华门左尽左第一铺、西至西上南北门左,西华门右尽右第九铺、西至西上南北门右。西安门左外尽左第十二铺、内至乾明门左,西安门右外尽右第七铺、内至乾明门右。以上该金吾右、羽林右、府军右、燕山右四卫官军分守。
玄武门左尽左第五铺、北至北上门、北上西门以左,玄武门右尽右第四铺、北至北上门、北上东门以右。北安门左外尽左第十二铺、内至北上西门外以左,北安门右外尽右第八铺、内至北上东门外以右。右金吾后、府军后、通州、大兴左四卫官军分守。 [74]
此“皇城四门”,绝非内城诸门,而是各内外城门构成的四个瓮城防卫系统。常欣据此指出:“不论‘内皇城’还是‘外皇城’,都是由所在卫军按区分守……并不以内外而定界。” [75] 的确,此段与正统十三年(1448)文件一致,按“皇城四门”即四方分工。区别在于,文件罗列每区的防守要地,而《会典》勾勒每区的各段防线,防线以内、外两门为枢纽,向两端、左右延伸,最终彼此接合。
南部防线分午门前方与两侧、端门至承天门、承天门两侧三段。各段无缝对接,形成两个背对背的U型。若不计外围各铺,防线所围,正是南部瓮城。
东部防线分两段,内以东华门、外以东安门为核心,除各沿城墙延伸,相向沿东西甬道两侧,在东上门“左”“右”与东上南北门“左”“右”接合。这印证了东上南北门临甬道而设的推测:“东上门左”与东上北门左、“东上门右”与东上南门右,需南北两门临街,方得唇齿相依,令东区防线对接。若不计诸铺,防线所围,正是东华门至东安门之间的甬道。
西部防线,内由西华门外至西上南北门,外由西安门内至乾明门,未曾衔接。西部,盖因内外门之间距离太远,放弃了中间南北向的乾明门至西上北门一段,分守西安门内、西华门外两段。西安门内防线起止,正合上文所述的棂星门东西封闭空间。而西华门外防线,至西上南北门即路口而止,未达西苑门。西苑门虽与西华门构成封闭空间,毕竟不在西华门至西安门的道路上,或因此无需防守。而晋宏逵据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指出:“紫禁城西侧,北自乾明门南到东华门大街北,一条南北向长墙隐藏在房屋群中。” [76] 明代若在此段设墙划界,守卫出西华门北转至乾明门一段,亦属合理。
北部防线,由内城北墙、玄武门向外至北上门、北上东西门,由外城北墙、北安门向内至北上东、西门,内外接合。内外防线各形成两个不规整的背对背U形,比东西部复杂。其中,“北上门、北上西门以左”之“北上门”,似指经过北上门至北上西门,颇显冗余。其实,此含北上门“左”之意,指只能按“北上门左”计的、北上西门向南延伸到护城河的那段城墙。若不计各铺,从玄武门到北安门,本应围成一个长长的瓮城,防线呈两个规整的背对背U形。因万岁山阻隔,其东西北三侧的道路需纳入防区。故北安门为枢纽的北部防线北段,沿三侧道路延伸,在北上东西门与南段会合。如上述,北上东西门可视为北上门外的十字路口,此正合东部防线的结合模式。
总之,北京皇宫城池的守卫任务,不但按四个方向分派,而且每个方向的防区和防线,契合上文所示诸封闭空间。可以想见,若无万岁山和太液池阻隔,北方、西方的防区防线,会像南方、东方那样,完全对应各甬道。全城守卫的重点,并非内外城的城墙,而是内外城之间的通道,相当于南京的四大瓮城地带。
正德《大明会典》每一节,一般先录 “洪武二十六年定”即《诸司职掌》原文,再记历年“事例”。此“守卫”一节,无《诸司职掌》原文可录,先简介守卫事务,再列各卫分守地段防线,以下方列“事例”。所以,此乃高于后增“事例”的基本制度条文。如上述,南部防区八卫,乃永乐十八年(1420)四旧加四新,四旧来自洪武上十二卫,四新来自靖难后新设十上直卫。其他三区,每区仅四卫,每四卫乃两旧两新。如东区的羽林左卫、府军左卫属洪武上十二卫,金吾左卫、燕山左卫属新设十卫。由此,北京的二十卫系统,是由南京的十卫系统翻倍而成。洪武时期的上十二卫中,锦衣卫、旗手卫职掌内廷服务,本非守城之军。但传统的上十卫中,府军前卫是蓝玉的起家班底,洪武二十六年(1393)遭彻底清洗 [77] ,必不能再任宿卫,此后当由旗手卫接替。则南京皇城的防卫,本分四个防区,每区一个金吾或羽林某卫、一个府军某卫,南方加旗手卫、虎贲左卫,十卫分为四、二、二、二。可见,《会典》所记分区模式和兵力配备,乃沿袭南京旧制,永乐迁都以来沿用不移。万历《大明会典》相关部分,沿袭了正德《大明会典》原文 [78] 。总之,明代皇宫城池的防卫体系,一直基于以四个内外城门为核心对接防线而成的瓮城系统。
(二)瓮城式门禁
内外城之间,诸门层层叠叠、正跨侧分,但甬道区域毕竟是通衢大道,东部甬道更是官民频繁出入之所。与垂直交汇的诸便道相比,甬道会有更严格的肃静封闭措施吗?诸门会不嫌繁琐,像东华门、东安门那样设置严格门禁吗?刘若愚《酌中志》载:
骑马,凡内府有名骑马者,自东、西下马门起,至北安、西安门栅栏、东上北门止。又,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止。 [79]
内外城之间,只有某些指定道路区段可以乘马,即禁例稍松。此“东、西下马门”,不见他人记载。刘若愚《明宫史》又载:“内承运库……在东下马门。” [80] 内承运库,实在东华门外南北便道北段 [81] 。前引刘若愚介绍乾明门南道西,至西上北门,续曰:“其东向北者,则西下马门矣……西面城河,两岸止有矮河墙,罗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贤擅政,乘兴大工之际,辄自西下马门迤北,乾明门迤南,于兵仗局对门一带,造作房屋数区,以为秉笔直房,于风水颇失宜。” [82] 西上北门之“东向北”,已在护城河上,似不合理。按,魏忠贤建设的直房,仅“数区”,位于道路北端“兵仗局对门”,占据“西下马门迤北,乾明门迤南”。则“东向北”,不是指西上北门以东,而是介绍道西诸衙门完毕,开始介绍道西之东、便道之上朝北开的西下马门。此跨南北便道北段偏北的方位,正与东下马门对应。
按《酌中志》所述,从两处下马门骑马出发,往北、往西可达外城门,门以南便道不能骑马。但“东上北门止”,又似可骑马。宣德三年(1428),杨荣等“游万岁山……即入东上北门,乘马,及乾宁门,下马。” [83] 乾宁门不见记载。杨荣所游,即俗称万岁山的西苑琼华岛,此“乾宁门”必即上述琼华岛南小城的东门乾明门 [84] 。杨荣至此,必经内城东北角一带的东下马门处。此时或尚无下马门之设,但东上北门以北的便道,的确可骑马。崇祯十六年(1643),阁臣蒋德璟等赴景山:
出会极门,过文华殿、端本宫,过东华门,出东上门。上预传锦衣备马以俟,入东上北门,赐骑马。绕禁城外,而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行可千余武,折而西,过禁城,则万岁山在望矣。复折而北,下马,入山左里门。
出山左里门,复骑马,至东上门北门内,下马,步行入阁。 [85]
“东上门北门”,或为“东上北门”之讹,或东上南、北两门,本属东上门“系统”,故有此称。蒋德璟记事,极其细致,而来回东上北门至山左里门之间,未记下马。则明末之东下门马,或仅需过门下马,甚至对权贵重臣无实际妨碍。
西下马门的功能,应与东下马门一致。但刘若愚言“自东、西下马门起……东上北门止”,并未言“西上北门止”。明代记载中,也未见在西上北门以北便道骑马者。此西部南北便道,属西华门与西安门之间通道,或重于东部便道,与乾明门至西安门相当。上引杨荣至乾明门下马,似乾明门以西的小城不能骑马。但宣德八年(1433),杨士奇等十余人游西苑,“自西安门入,听乘舆马,及太液池而步。” [86] 途经棂星门等,未言下马,则杨荣于乾明门下马,只因到达太液池而已。乾明门与棂星门之间的小城乃至以西甬道,皆可以乘马,符合刘若愚所言终点“北安、西安门栅栏” [87] 。则西上北门以北的便道,与此规格相同,当可乘马。
“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止”句,似指可骑马绕内城南半圈。若然,当按顺时针顺序,先述宝钞司、后述终点西上南门。且内城以南的瓮城规格隆重,午门、端门一带,必不可骑马穿行,故此句不通。刘若愚此句,另有版本作:“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止,至宝钞司。” [88] 此句亦不通,然“至”字或有所自。颇疑两种版本皆存抄刻讹误,本意当为:“东上南门起,至南内;西上南门起,至宝钞司止。”即两条南北便道的南段都可以骑马。
嘉靖前期,夏言有诗“迎和门外据雕鞍” [89] 。崇祯十五年(1642),蒋德璟入对西苑,自内城入苑、苑内、归至内城,皆曾骑马:
出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上马,锦衣校尉执鞭。
登紫光阁……沿西海行,待马,过万寿宫,而锦衣控马至矣……下马徘徊久之。
时日已西……乘马出西苑门、西中、西上,至西华门下马。 [90]
蒋德璟从万寿宫往南一直骑马,与夏言诗对照可知,棂星门西与甬道垂直的南北便道,亦可乘马。但是,东、西华门正对的甬道,规格不同。蒋德璟赴景山,在东上北门外上、下马,东华门外舆马之禁甚严。此番锦衣卫没有在西上南北、门一带备马,而是在西苑门外等候,则西华门至西苑门的甬道不可乘马,同东部。但蒋德璟归时,又从西苑门一直乘马至西华门,或因外出时遵制,归时则已晚,又或因西苑门以东已非守卫区域,故不甚严格。结合刘若愚所载,可知东、西华门外的两处甬道,按规定本是不能乘马的。
总之,外城之中,与诸甬道垂直的大型便道,乃至西安门、北安门内,皆可乘马,规格一致。唯独东华门外至东安门、西华门外至西苑门的长方形甬道,不可乘马。万历三十五年(1607),皇亲陈承恩“以空舆出东上门,为伍长所缉……并提门金吾、羽林西上门诸指挥、伍长罚谪有差。” [91] 东西甬道的“马禁”“舆禁”,似同午门外的瓮城,和北上东、西门之间的小瓮城。换言之,四个内城门外的区域,无论是甬道还是瓮城,禁行规格皆遵瓮城之制。
在南京,洪武十年(1377)设守门内官,东西北每个方向有四门,如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北门 [92] 。十八年(1385)设门吏,每门四名,东西北每个方向有三门,如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 [93] 。守门内官与门吏,设置地点、职能不同。
门吏本设在横跨甬道诸门,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置依然 [94] 。正德《大明会典》载门吏设置、数额,较洪武时期有所调整,共十六门,增加了长安左右和东上南北等四个侧门 [95] 。《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十二年(1488):
铸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右、东上南、北、东中、东、西安、北中、北安并内府北安门照出入大小铜故关防印子三十七颗,以旧木石印子缺坏也。 [96]
此较正德《大明会典》少五门,似删并诸上门等次要者。但万历《大明会典》详载成化二十二年(1488)定制:“令各铸关防,凡钱粮文书进出用使。”各门门吏、关防数量不一,仍共十六门 [97] 。则《实录》系省文,所有跨甬道诸门此后依然皆设门吏,关防由木石改铜,盘查钱粮文书进出。
守门内官,本设在瓮城正侧各门,历代有增无减。明代中期,重申旧制职责为:“提督卫士,关防出入。” [98] 即内官率军人把守。天顺元年(1457),诸臣自述夺门功:“夺东中门、东上南门,直抵南宫。”“各藏兵器,夺取东上门,直抵宫门。”天顺六年(1463),有人发疯“突入御用监……复走入西上门,门者获之。” [99] 可知军人把守并非具文。崇祯十六年(1643),阁臣蒋德璟等赴景山观射:
其跟从人役,每员计一人,随入东门里,不得过山左门。各给司礼监木牌一面,预派内臣四员,在东上左门北察点。 [100]
随行者可以从“东门”即东安门,进至山左门即“山左里门”之外,需西过东中门,至东上北门转北。而路上接受盘查的地点“东上左门”,正是例设守门内官的东上北门。
诸门设门吏、内官及军人,规格高于内外城之间其他地区诸门,如上述黄瓦东西门、山左右里门、东西下马门甚至构成小城的乾明门、棂星门等。跨甬道而设的上门、中门、外城门,当与规格更高的四个内城门,构成“皇城四门”系统,门禁独严。而东上南、北门,乃临甬道而设的侧门,却兼设内官与门吏,规格直逼东安门、东上门,高于东中门、东安里门及其他侧门。可知东华门外,人员往来频密,尤重甬道内外之防。如上文,南京西华门外甬道的侧门,专为瓮城而设,背后临衙署,而非背开街道。而据上引杨荣出北上东门骑马,可知明初建北京,即在侧门背后开南北便道。此较南京稍轻瓮城之防,而重甬道内外之交通便利。然诸门设守门内官、门吏,在东部整条甬道和西华门外、玄武门外、北安门内、西安门内等封闭区域,仍围成人员、马匹、车辆无法自由通行的空间,虽由衙署围墙取代了特设的瓮城墙,封闭效果则近似南部午门至承天门的瓮城。
四、结论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的内外两重城池,并非出自规划,而是明初两次承旧创新建设的偶然结果。中国古代的皇宫城池,本无内外双重城墙的规制。金中都的皇宫城池,继承唐宋的北宫南衙之制 [101] 。元上都的皇宫,的确建内外两重城池,内宫外衙。但外城分布着诸多官署、寺院和作坊,面积占全上都城一小半,显得上都城倒算是外城的附属部分 [102] 。则此外城,更似后周、北宋的州城,不能视为典型的皇宫城池。在元大都,外城称为萧墙、外周垣、阑马墙,只为环卫东西两个宫殿群而建,性质实似六朝建康台城的城墙:结构有相邻多层,功能仍只算一重。但是,元朝虽然没有刻意建设两重城池,却不得不圈入大片苑囿,无形中造就了比内城大得多的外城,则与上都、建康迥异。明初定都南京,必承南唐、南宋以来的“旧内”规制,建单重皇城,为强化防御在四面增建巨大的瓮城。攻克元大都后,又仿元代体制,增建外城,原有瓮城的外端城门,正是现成的外城起始点。永乐年间,这个内城加瓮城为主、外城为辅的格局,被照搬到北京。北京皇宫城池的建设,不再体现南京内外城的主次先后,外城因包涵西苑、万岁山而尤其庞大,遂呈现为内外两重城池的样貌。
明代北京皇宫城池,貌似内外两重,实具南京瓮城遗制。南京联通内外城的瓮城,侧门规格高而居中,围墙严整封闭,建设早于外城。故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可称前所未有的内城加四面瓮城之格局。北京的东、西上南、北门,紧临甬道而设,棂星门西有类似东西上南北门外的南北便道,北中门与北安门分据街道两端,北上东、西门相当于临十字路口而设,在内外城门之间的四个地带,围成多处规整的封闭空间。它们已非南京那样的瓮城,但亦非开放街道。宫廷的防卫,不是按内外而是按四方划定防区,内外城门同为各区枢纽。诸封闭空间与防区、防线高度吻合,禁行规格直逼南部瓮城,门禁森严,比内外城之间其他地带更具“内”的色彩。凡此,皆非内外两重城池之规划布局可以解释,而是南京瓮城结构的孑遗。
内城配四大瓮城的整体图景,即不分内外的“皇城”,可能是明代前期对皇宫城池的主流认识观念。在南京的设计者心目中,皇宫城池是一个内城向外伸出瓮城的整体,瓮城与内城门密不可分,瓮城的城墙与外城门仍是内城的一部分。照此,外城门首先不是外城墙上的大门,而是以内城门为起点的瓮城顶端的城门,外城只是增建的、附属的、划进大片官署的“皇墙”。对北京的一般人而言,面对皇宫城池,首先看到的是外城门,进门即算进入“皇城”。但他进入的是瓮城或封闭空间,面临重门叠嶂和两侧墙垣,无暇感受到内外两重城池。即使内城巍峨远超外城,也不再像元代那样醒目,不易被视为外城的对立物。这种内外一体的感受,支撑着以外城为界的整体“皇城”观念,贯穿明代始终。
按当代观念,元明清三代的皇宫城池,皆分内外两重。但明代前期,内城加瓮城、内外一体的整体观念才是主流。此后,因为瓮城的淡化,随着外城门禁松弛、向民间开放,内外两重的观念才慢慢演进,直到清代定型。皇城的诸多重要演变,如明代中后期内城的名称更替,明清内外城门的俗称流变,乃至南京外城门长存俗称的现象,皆与明代皇宫城池原初的瓮城结构及相关观念,息息相关。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 例见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六朝建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98页。
[2] 宋敏求著、辛德勇点校:《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
[3]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4-477页。
[4] 明清以来,对皇宫城池的称呼,有“皇城”“宫城”“禁城”“大内”等,所指不一。本文姑以“皇宫城池”指整体,以“外城”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以“内城”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以免歧义。
[5]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第1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6] 王剑英:《明中都》,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46页。
[7] 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8] 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第87页。
[9]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251页。按,朱偰指出,“东西”系“南北”之讹(《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页),今据改。
[10] 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11]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癸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台北,1962年(本文所引明代历朝实录,下同不注),第622页。
[12] 杨平:《从元代官印看元代的尺度》,《考古》1997年第8期,第89页。
[13] 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河闸关梁·望云桥”“河闸关梁·马市桥”引徐维则藏抄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98、100页。
[14]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74-477页。
[15] 例见宣德三年(1428),顾佐上奏:“萧墙之外置铺,夜巡提铃达曙,已是定制。今臣每于四更来朝,而长安右门诸铺,提铃已绝,旗军熟睡。”(《明宣宗实录》卷四六,宣德三年八月乙巳,第1135页)天顺七年(1463),明朝“修大明门、正阳、长安左右等门道路、萧墙守卫直房。”(《明英宗实录》卷三五四,天顺七年七月庚子,第7080页)
[16]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七《工部·营缮清吏司·营造·城垣》,影印明万历刻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2549页。
[17] 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第83、128页。
[18]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六二《工部·宫殿·皇城之制》,影印清嘉庆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4482页。按,万历《大明会典》不载外城规格,而清历朝官书皆记内外城规格,其中内城与万历《大明会典》一致,则所记外城规格,应即明代外城规格。唯历朝所记,略有参差,其中嘉庆会典较完整可信。
[19]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门考》,第161-164页。
[20] 《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收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一,影印明永乐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叶17a。按,收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点校本,略存遗憾。本文正文取《永乐大典》本,图取影印清抄本,别以页码标识方式。
[21] 《洪武京城图志》“皇城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页。
[22]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4-155页。
[23] 王樵:《方麓居士集》卷十一《金陵杂记·皇城》,明万历刻本,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叶1a-b。
[24] 《洪武京城图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第32页。
[25]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旧丞相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影印明万历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00页。
[26] 《明武宗实录》卷一〇〇、一六五,正德八年五月壬午、十三年八月庚辰,第2081页、3199页。
[2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第1901页。
[28]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第2657页。
[29] 郑明选:《郑侯升集》卷二四《为窃盗潜入内地查参守卫官员乞加究治以严法纪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5册影印明万历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6、429页。
[30]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八三、一一六,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十年十二月戊申,第379页、1481页、1901页。
[31] 王剑英:《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1年),收入王剑英《明中都研究》,北京:青年出版社,第207-460页。
[32] 《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丁卯,第936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第1481页。
[34] 《明太祖实录》卷三五,洪武元年九月戊申,第628页。
[35]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酉,第3227页。
[36]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第136页。
[37] 梁庆华、邢国政:《南京明故宫范围有多大》,《南京史志》1989年第6期,第41-43页。
[38] 参见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第81-84、88-91页。
[39]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1页。
[40]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41]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8、165页。
[42]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43]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五,景泰元年八月庚辰,第4119页。
[44]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
[45]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1-142页。
[46] 按,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标在东南(“明皇城”,第34页),本文发表稿据以推论,李小波《西苑与嘉靖政治》推测在西南(待刊),是。本文现据李文修改,未影响关于南北便道和构成甬道的结论。
[47]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二《宸翰》引明世宗文,《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54册影印明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76-1577页。
[48] 夏言:《夏桂洲文集》卷六《西苑进呈诗二十四首》、卷七《浣溪沙·壬寅正月十六日见东宫踏冰过金海作二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影印明崇祯刻本,第310、347页。
[49] 严嵩:《钤山堂集》卷十六《诏赐金海乘凉诗·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41册影印明刻本,第607页。
[50] 《明内廷规制考》卷一《宫殿额名》,《丛书集成新编》第29册影印清《借月山房汇钞》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附载宫殿额名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7页。
[51] 按,据上引夏言、严嵩载,由此道一带可直达太液池,故太液池西应无《北京历史地图集》所标墙垣。
[52]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9页。
[53]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54]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第9-10页;许冰彬:《明代御用监考略》,载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刊》第1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55]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56]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6-147页。按,“广和门”应“广和右门”简称。又,“之北”,据上下文体例、文意补。
[57]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
[58]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59]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7-138页。
[60]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宣德四年六月壬辰,第1315页。按,“卫”,原本作“军”,应系抄写讹误,据文意改。
[61]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9页。
[62] 单士元:《故宫史话》,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63] 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八《礼部·祠祭清吏司·丧礼·公主》,第1532页。
[64]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57页。
[65]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庚戌,第2242页。
[66] 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影印明正德刻本,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559页。
[6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二九、一四三,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十五年闰二月甲申,第380、2054、2243页。
[68]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五一,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辛未、永乐四年二月戊寅,第136、765-766页。
[69] 《明仁宗实录》卷九上,洪熙元年四月丙午,第284页。
[70] 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第87页。
[71] 叶盛著、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二二《守卫四城官军揭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0-221页。
[72] 按,实应二十卫,叶盛作“二十一卫”,而只列出十九卫。查,叶盛漏掉了燕山右卫。
[73] 《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收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一,影印明永乐抄本,叶17a。
[74] 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八《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第559-560页。按,同书同卷载,内围二十八铺,外围七十二铺。而此处内围诸铺相加,为四十一铺,外围相加,为八十四铺。万历《大明会典》则照录此段,又称内围四十铺,外围七十二铺,似正德《大明会典》讹。但《明熹宗实录》载,外围七十二铺,内围二十八铺(卷六七,天启六年正月辛未,第3205页),反而合正德《大明会典》。合计与记载异、诸载彼此抵牾,殊不可解。观各方左右铺数不一,多合城墙长度。如东、西华门偏南,右仅一铺,左则十铺左右。西安门偏北,右仅七铺,左则十二铺。长安右门往西较长,有十一铺,长安左门往东仅六铺。唯东安门偏南,而左右皆十四铺,则右即南“十四铺”之“十”或讹。但即使如此,总数仍非七十二。又,内外合计数,比文中直载,多十二、十三。或四角、诸门有重复计算?志此以待解惑。
[75] 常欣:《紫禁城守卫与红铺的变迁》,第87页。
[76]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第165页。
[77] 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57页。
[78]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三《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第2005-2006页。
[79]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第168页。
[80]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内府职掌·内承运库》,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46页。按,刘若愚《酌中志》,有《海山仙馆丛书》本与清内府抄本,冯宝琳据以整理。另其中五卷单行,名《明宫史》,北京出版社据其清《学津讨原》本,与同书名《芜史》明抄本整理,又配以《酌中志》之《海山仙馆丛书》本内容,而未列校勘记。五卷单行的《明宫史》,文字颇有不见于《酌中志》者,但北京出版社整理本或据《酌中志》之《海山仙馆丛书》删改。今尽量取《明宫史》北京出版社整理本,若必要,取《学津讨原》本或《芜史》明抄本。
[81]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82]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9页。
[83]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一《赐游万岁山诗·序》,《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29册影印明正德刻本,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19页。
[84] 按,雷礼等述此事,即改为乾明门(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九《内阁大学士行实·杨荣》,《续修四库全书》第552册影印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85] 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慤书》卷九《万岁山观德殿召对恭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3页。
[86] 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十五《赐游西苑诗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08册影印明天顺刻本,第940页。
[87] 按,刘若愚此句,另有版本作“西北西安门栅栏”(《明宫史》水集《内臣服佩·骑马》,《丛书集成新编》第85册影印清《学津讨原》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第686页)。此指骑马终点为西北方的西安门内,北中门至北安门似不能骑马。但是,据前引宣德四年(1429)从北安门上奏受阻于北中门,可知北中门内的门禁规格高于门外,门内可骑马,门外当可。
[88] 刘若愚:《明宫史》水集《内臣服佩·骑马》,《丛书集成新编》第85册影印清《学津讨原》本,第686页。
[89] 夏言:《夏桂洲文集》卷五《雪夜召诣高玄殿》,第299页。
[90] 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慤书》卷五《西苑明德殿召对赐宴侍坐复观火箭恭纪》,第48-52页。
[91]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五,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甲戌,第8228页。
[92]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第1901页
[93]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第2657页。
[94] 《诸司职掌·吏部·选部·官制·吏》,《玄览堂丛书》第三册影印明刻本,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1762页。
[95] 正德《大明会典》卷六《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吏》,第86-87页。
[96]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〇,成化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第4719页。
[9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三《兵部·车驾清吏司·守卫》、卷七《吏部·验封清吏司·吏员》,第2010、138页。
[98]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巳,第190-191页。
[99] 《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二七五、三四一,天顺元年正月己丑、二月乙未朔、六年六月癸巳,第5817、5832-5833、6928页。
[100] 蒋德璟著、粘良图点校:《慤书》卷十《万岁山亲阅勋爵较射恭纪》,第95页。
[101]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金中都”,第24页。
[102]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