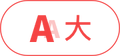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余英时先生】
8月5日刚刚在北京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回来,正闭目养神,我家老张突然慌张地跑来告诉我,余英时先生于睡梦中逝世了。太突然了,深感震惊和悲痛。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普大访问硏究期间,得到先生及嫂夫人多方面的亲切关心和照顾,得以完成《朱熹哲学思想》一书。在新加坡完成的《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也是在普大修订並最终定稿的。两本著作余先生都热情作《序》,亲自带到台湾出版。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
余先生和钱穆先生一样,对历史悠久而光辉卓异的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温情和敬意。在海外执教和著述数十年,为推广和提高中国文化和学术在世界的声誉和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获得的诺贝尔式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大奖,实是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最好肯定,是余先生对中国文化学术作出的卓越贡献。
先生心怀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对两岸中国学人的成长,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在美国的学习和学术交流,争取资源,创造条件。大陆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都受到先生最大的帮助。
先生的重要著作在大陆大量出版,极大地开阔了学人的眼界,树立了学术研究的高标准范式,是对大陆学术界的最大帮助。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到《中国古代士阶层史论》,即受到极大启发。《汉代思想史》的写作与此书有内在的关连。先生的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提出“道统”、“内圣外王是一个连续体",也打开了我硏究朱熹的新视野,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来阐发这一思想。受惠的大陆学人都从先生的著作中吸取了教益。
在普大我亲见先生对大陆学人的关心。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为中国文化培养“读书种子",以期它的健康成长。
文化学术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关心故土吾民,莫过于帮助它的健康成长了。先生之为当代大儒,正在于卓越地担负起了为民族文化复兴而竭尽全力的历史与时代使命。
“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文化之生命活力正在于每一时代,都有杰出的独领风骚者为之弘道。余先生是我们时代人文学术领域的独领风骚者。他的著作和精神,将使后学受惠于无穷。中国文化之富于生命活力,余先生正是最好的见证。
余先生是在睡梦中与世长辞的,这是上苍给智思大德者的礼遇。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智思不倦的马克思就是六十七岁时在书卓的椅子上溘然去世的,孔子好像也是在梦游中与世长辞。不少高僧大德的圆寂,也是如此。这更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极大敬意。好像一个人,上苍派他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任务完成了,就接他回去了。西方伦理学讲德福一致,讲“圆善”,先生的去世可谓“圆善"的见证。
神而静谧兮,哲人其萎。
梦而魂离兮,上苍礼请。
善始而终兮,世所罕见。
三立不朽兮,史册永存。
请嫂夫人节哀
我曾在2019年12月23日写有《倡明国故,融会新知——我和余英时先生的以“以文会友”》一文,首托友人转《南方周末》,不能发表,惠请转给余先生,但石沉大海,音讯全无。现特附于后。
金春峰敬撰 2021.8.6 北京风度柏林寓所
敬挽英时先生
大儒风范,光跃照人。
笔锋凌厉,大爱藏心。
著述等身,不愧民魂。
和恕东风,时雨常临。
呦呦鹿鸣,嘉宾如云。
嫉恶如仇,直道而行。
愽雅君子,东西贯通。
济济多士, 受教於门。
文史会萃, 风骚独领。
风雨岁月, 惠我以情。
寒夜相迎, 特暖我心。
暗潮洶涌, 护我前行。
两《序》相送,学界扬声。
安详辞世,笑容永存。
捧读遗著,泪不自禁。
《以文会友》,今世之幸。
高山仰止,独惟伊人。
金春峰敬挽
2021.8.6
北京风度柏林寓所
【附: 倡明国故,融会新知 ——我和余英时先生的以“以文会友”】
余先生《会友集》(2008年明报公司出版)中,收有关于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我的《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时代与文化》所作《序》,一篇是为我的《朱熹哲学思想》写的《序》。
余先生于我,实乃亦师亦友,首先是师,然后是友。我1988年于新加坡东亚学术会议上见到先生前,已先读了他的“文”,并受到很大启发。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汉代思想史》时。写完了西汉中期的《盐铁论》后,在李泽厚先生处,看到了余先生的《中国古代士阶层史论》。翻阅之下,如获至宝。李先生学识和交游广阔,不知他从那里得到了余先生的这本大著。书中关于汉代“几大士族集团及其与刘秀的关系”一文,让我眼界为之一开。国内当时盛行的是老的豪族观念。局限于此,士阶层在“独尊儒术”以后的巨大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就被遮蔽和忽视了。东汉的兴起与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内在关系也会在视界之外,而不能洞悉其中动因之奥祕。我立刻引用了“士族”这一观念,用以解释王莽的兴起与覆灭、东汉经学的兴衰及党锢之祸的社会阶级原因。可以说,《汉代思想史》东汉部分的成功,显得有声有色,要归功于这一观念的启发。“启发”是很重要的。这是“新知”,像一把锁匙,有了它就可以登堂入室。像一道闪电,可以籍此看到那在暗处不明的东西。写作须要灵感,这观念真正触发了我的学术思想灵感。像三峡之水开了一道阐门,喷湧而出,直贯到了东海。当时真有疱丁解牛,技进于道,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感。那种精神的愉悦,今天似还留心间。盖中国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内圣外王一体两面”,它和政治、经济是紧密结合的。体现和推动这种结合的社会力量就是“士阶层”,在汉武以后,就是新兴的“士族”。没有“士族”这一概念,东汉的政治和思想发展就没有支柱与中轴了。《汉代思想史》写作于1983至1986年,1987年出版。在《后记》中我特别记载了这一大亊。
“1984年5月,从汤一介同志处借到了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10月从李泽厚同志那里看到了余英时先生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先生提出的‘土族’概念,我在本书中引用极多,成为分析宣元时期儒学确立统治地位与东汉经学衰落的重要概念之一,更需在里特别提出。虽然“士族”不是新的概念,但国内学术界一般认它的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并未应用于分析西汉和东汉初期的历史现象和思想学术问题。“
1988年5月,我应聘为新加坡东亚哲学所高级硏究员。是年8月所里主持在新加坡举行了盛大的东亚学术思想国际硏讨会。余英时先生来赴会了。会议间隙,我和王心扬先生特定去拜访了先生。这才略知先生的风采。没有想到,1990年我竟意外地到余先生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作访问学者了。东亚所这边是林毓生先生推荐的(当时和我一起在所里作硏究),美国方面就是余先生。1990年元旦,我飞离新加坡,因飞机故障,临时降落迪拜,躭误了在伦敦的转机时程,到纽约已是延误了一天的深夜了。从机场打电话告知余先生,先生和嫂夫人午夜以后等候在汔车埸接我。寒风凛烈,先生为我临时安排在硏究生宿舍过夜。此景此情,历历在目,深为感动。在给先生的信中,我曾引《诗》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是新加坡忆旧,一是感概赴美行程。不料在此一待,竟几乎八年之久。
我在新加坡近一年零七个月,写完了《〈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时代与文化》一书,稿件带到美国。经整理后即请先生审阅,並请带到台湾,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余先生为书稿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并书名题签。盛情出乎我的意外,评价也出乎我的意外。原来余先生对《周官》早有硏究并有浓厚兴趣,一直高度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周官》之成书,关乎汉代的经学史,关乎王莽改制、篡权,关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也关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及钱穆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1978年余先生率美国汉学代表团访问大陆。先生的《日记》写道:“11月14日,代表团中的大多数成员用一天时间游览了长城和明代皇陵,杜敬珂留在北京和历史所的史学家们交谈。”《顾颉刚日记》11月13日写道:“今晚历史所来电话,谓美国汉学家集团定明日上午到所,讨论‘汉代今古文经学问题’,我既病,只得由起釪往,因嘱其先读我旧作《古史辨》第五册自序。”抱怨说:“中国学问须待外国人推动有如是者,不可叹耶!”我的《周官》硏究引起余先生的兴趣,是很自然的。但我当时並不知此背景。书稿由余先生带到台湾,由东大图书公司于1993年底出版。在夏威夷召开的东西方学术讨论会上,余先生赞誉了这一著作,王元化先生参加这一会议,会后来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开会,见到我,转告这一情况。
我的《周官》硏究计划是到新加坡后定的,利用了云梦秦简等出土文献,以二重证据法,证明《周官》反映了许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制。其田制、乡隧、财税、啇业、祭祀、丧葬、法律、时暦、货币、官职职守等,只有运用云梦材料,才能得到确切了解,如墓葬以“爵等为其封丘之度与其树数”。“树数”两字,《礼记》等典籍无其说,惟《商君书》有此规定,等等,从而指出了郑玄《周礼注》的不少误注,结论是:这是战国末年山东六国入秦的学者所作。对徐复观先生《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进行了批驳。徐认为《周官》乃王莾刘歆共同伪作。书在台港海外得到很大重视。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要在大陆出版。可惜版权已完全给东大了,没有成功。国内硏究《周官》的一些学者不知有此书,仍然论断《周官》为西周著作。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学术交流之重要。只有融合新知,才能真正倡明国故。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主要研究朱熹,于1997年完成《朱熹哲学思想》一书,亦请余先生作《序》,1998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基本观点是:朱亦是心学,不过风格与具体论证及说法与陆王心学有所不同而已。余先生实早已对朱思想作深入研究,对朱为心学是不赞成的,在《序》文中虽未明言,但2002年他在台北联经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哲学观点上是采当时学界的主流如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我则持与冯先生对立的看法,可谓逆潮流而动。故余先生本其长者的忠厚之心,在《序》文末尾特地写道:“金先生投入信仰的态度则十分明朗。他对朱熹的理解和冯先生大相径庭,是事有必至的。信仰是个人之事.决不在讨好时风势众。此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在这一点上,我愿意郑重向学术界推荐这部《朱熹哲学思想》。”冯友兰先生是我北大作硏究生的导师,指导朱熹哲学硏读。我的毕业论文是“朱陆异同”,但我並未接受冯先生以朱乃柏拉图一类“共相论”思想之见解,而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名言行事。这无异于背叛师门,极有违于中国之传统道德,引来非议是必然的。余先生的话对我是一种鼓励,但我内心的精神压力却反增加了。先生特地提到“信仰”,是因我1997年在东大出版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一书,认为人不仅有理性,且有信仰。信仰对中国价值观的形成有重大作用,但中国哲学史研究都将此忽略了。书请汤一介先生和我的老朋友——美国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作序,收录了我的七篇论文。
1998年10月,我到中央硏究院中国文哲硏究所从亊“冯友兰哲学专题硏究”。书稿《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于2000年7月完成。我在《自序》末尾用小诗写道:
“十年教诲岂敢忘,下笔评论费思量。
独立思考先生倡,尊师更当道弘扬。
众人传薪火焰高,抛砖引玉是所望。
后浪前浪相激扬,浩浩大江奔东方。”序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6月28日,2001年2月8日改定。反映我的内心是挣札而不平静的。
余先生《朱熹历史世界》是从历史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朱熹思想及其与两宋政治的关系作细緻的梳理。朱之哲学学思想属性基本不在讨论的视线之内,故采学界主流的看法,并不影响书的完整论述。大著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除正面肯定的评论外,也有刘述先、李明辉、杨儒宾先生等的批评质疑。我亦在《九州学林》上连发两文参与论争。
《朱熹的历史世界》对我启发很大的是其专章论述且极为重视、极有份量的“道统”观点。这为我的朱熹硏究开辟了一新的视域。我原来的硏究是按传统方法,就哲学论哲学,专作概念分析而完全离开政治的。“道统”按余先生的提法,“内圣外王是一连续体”,我则进一步概述为乃“一体两面”。故有如“士族”概念对我汉代硏究之重大影响一样,“道统”也成了我此后硏究朱熹思想的重心。除《九州学林》发表的两篇,又写了《朱熹与南宋的政爭及党爭》、《朱熹〈中庸章句〉的诠释方法》、《从周敦颐到王阳明——以“道统说”为中心》等论文。近年批评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的《宋明理学论纲》,也继续运用与发挥“道统”思想。可以说“朱熹思想”这个“国故”,就我而言,也是融会了余先生提供的“新知”而更进一步加以倡明的。
何谓“道统”?“统”有纵横两方面的意义。横的“一以贯之”是“统”,纵的“创业垂统”亦是其内涵。“道”即儒家“内圣外王不可分割”之“道”。对“道统”内容的具体了解,自韩愈至北宋苏轍、程颐等各有不同。朱熹才正式确定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十六字心传”为“道统”内容。传“统”之系列,朱在尧舜以前加上了伏羲,神化“十六字”为伏羲“继天立极”而得的圣神大经大法。尧舜等圣帝明王政教合一,完整地贯彻与体现了“道统”,孔子则有德无位,不能政教合一,仅成为“道统”之学——所谓“道学”的传人。“道学”的内容是什么?我认为仍是“道统”的“十六字心传”,仍是“内圣外王一体两面”之整体。故对余先生孔子乃“传道之学”,及“朱熹仅发展了‘内圣’方面”这一提法,亦提出了质疑。这可说是“以文会友”的表现吧。
这过程使我深深感到,“闭门造车”是不能使学术往前发展的。惟有不断融会新知,才能使其不断创新、前进。
2019.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