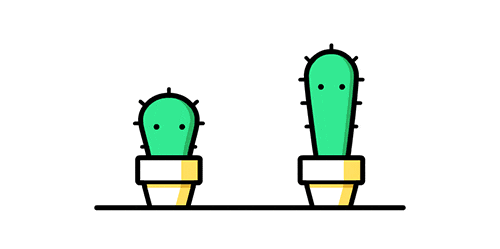我们大都错过了父母的风华正茂
不论是写作的密度还是高度,台湾的文学朱家都称得上是一个传奇。然而在家里最小的女儿朱天衣的眼中,这个“用稿纸糊起来的”文学之家,其内在的温情与细碎日常和寻常人家并无异样。在她的笔下,母亲是心怀文学梦却不得不为家庭琐事牺牲自我的“后勤司令”;父亲是常年伏案笔耕的文学信徒。
父母相爱,便是这个文学世家的开始……当作为女儿的朱天衣回望父母的“那些年”和这个文学世家的过去,她又会生出怎样的情愫呢?
母亲
刘慕沙(1935~2017),台湾苗栗人。作家朱西甯之妻,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之母。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三十余年,尤以翻译川端康成、菊池宽等人的著作闻名。
要多长的时间才足够,足够到可回顾母亲离开前的那段日子,足够到确定她已离去,足够到不再不时问自己她到哪儿去了,她到底到哪儿了。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后,我们陪她搭乘救护车转院至荣总安宁病房,一路躺在推床上的她歌唱不止,有她最爱的圣歌,有我们自小听惯的名曲,那时距她离世不到一百个小时。她神志清明知道所有的安排,也接受这样的安排,信仰甚笃的她明白这是必经之路。但死亡真正来临时,她不会有所疑惧?她一路高歌是为远扬壮行?
二〇一四年夏天,母亲喘息严重、呼吸困难,送入加护病房,先以为是感冒引起肺炎所致,后脱离险境转普通病房又住了三星期才查出是肾脏问题,排水不良造成肺积水方引发呼吸紧迫。出院后,又尽可能地推迟,但终究还是得接受洗肾治疗。洗肾后昏沉状态改善了,但随之而来的贫血、缺钙、缺钾、甲状腺异常、抵抗力变差等副作用,就此紧缠着母亲,也让照护她的姐姐时刻处在紧绷状态。
朱家姐妹和妈妈刘慕沙
一周三次,近两年的洗肾期间,饮食须严格控管,连饮水也须滴滴计较,但母亲孩子气的任性,始终不改嗜咸的脾性,总令二姐跳脚。每天须记录水分摄取及排出的功课,不耐烦数字的母亲,也总是能赖就赖给大姐。老年照护的疲惫无奈,在我们家一样没少,而这些重担都是由住在一起的两位姐姐担下了。
即便一家人,每份母女情都是不同的,二姐对母亲最是唠叨,到老也不放松对母亲的鞭策,要她长进,要她独立,要她深思所有,要她神志清明到最后一刻。这让倚赖父亲一辈子的母亲常感困顿,但从小到大,最护母亲的是二姐,陪伴母亲最多的也是二姐。
自小,大家都认为姐妹仨数我最像母亲,容貌像,性情也像。小时候,野野的、贪玩、爱养动物;及长,好客、好烹调,唯恐人饿着,屋内屋外的猫狗禽鸟也在管辖范围,不喂饱它们便是天大的罪过。从小家里食客不断,任何时刻进门,母亲总能迅速办置一桌菜肴让人大快朵颐。即便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较正式宴客,她也总能触类旁通地整治一桌令人惊叹的席菜,或是和父亲在外饮宴的复制品,或是从邻居妈妈们习来分不清哪个省份的变造品,多了她的想象创新,便形成了她的独特风格。
朱家全家福;前排右起:天衣、天心、天文
印象至深的是炸元宵、狮子头及小肉丸,那元宵经油炸后类似广式甜点芝麻球,但母亲大大咧咧不讲究火候,每每都炸开了口,便索性以“开口笑”名之;狮子头则是肉丸不炸不揉,直接和黄芽白、菇菌炖煮,软烂下饭下面,很合适牙口不佳的人食用,又因肉丸中添了豆腐及馒头屑,所以母亲称它是“穷人狮子头”;至于那若弹丸大小的肉丸反而费工多了,每颗都须又揉又砸二十余下,排整好蒸透了,煮汤、烩青蔬时丢几颗进去,便鲜美无比。然而大手笔的母亲动辄二三百颗起跳,我们姐妹常为这小肉丸砸到手都快废了,好在这丸子多只出现在过年,一年累一次就好。
说到年菜,母亲也常一窝蜂地跟着村里流行走,一年家里廊下出现了捆蹄,又不知是从哪省妈妈那儿习来,不等食用便长了绿霉,不敢食用又弃之可惜,遂任它继续恶化,直至生蛆为止。当然也有绝不会失败的常年菜及酸笋,这些是文友们多年后还念兹在兹的地道客家菜,但之后长居客家庄,才知这酸笋在以高汤烹煮前,须汆烫数次以去其酸涩。但母亲却省略了这道工序,顶多发泡汆烫一回,便丢入大骨汤中佐以大量酸菜熬煮,留其酸味,以杀年节肉食过度的油腻,这也是她率性下的产物,且一次必煮十来斤,就算每餐海碗伺候,那一大锅也可吃足整个年节,且越煮越滑润,还真百吃不厌。
平日餐点,母亲也以量取胜,猪脚、鲜笋、卤菜……完全像餐厅规格,一来我们姐妹仨胃口实在好,父亲看似瘦削,食量也不遑多让,不如此海量供应,实难满足一家人的脾胃;二来她常处赶稿状态,煮一大锅可省去许多工夫。然胃口再好,面对母亲的食海战术,吃食较精致的二姐便常生怨叹,父亲则笑道“吃得鼻子眼睛都是”,家里猫猫狗狗在同样喂食下也常吃兴缺缺。每当母亲看这些毛孩面对一缸食粮翻白眼时,便会叱道:“这不吃那不吃,要吃仙桃呀!”这总令一旁的我发哂,以为这话是说给二姐听的吧!
母亲另一身份是日译作家,从小便随着舅舅们看遍各式文学作品,连世界名著也是通过日文阅读的。她之所以和父亲认识、通信到结婚,文学相与是极大因素,成家后,连生我们姐妹仨,较不需完整时间的翻译工作遂成了她笔耕主力。她的译作多是川端康成、曾野绫子、远藤周作的作品,后来则是井上靖、大江健三郎,母亲是台湾极重要的日文翻译作家。
1959年家庭合照。后排左起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天心、天文
孩时,母亲常因赶稿误了我们姐妹的中餐便当,记忆中,和姐姐多次在校门口等待无人,直至午休钟响,才见她匆匆骑车赶来。嘴嘟嘟的我们总不解,做个便当有那么难吗?译稿再投入,怎会连电饭锅开关都忘了按(每次大延误都缘于此)?但当时若不是母亲译作如此勤,以父亲的军职薪饷及微薄稿酬,是不足撑持家中川流不息的文人朋友打牙祭的。
后来父亲提早从军中退伍专志写作,家里经济状况也略趋稳定,母亲便重拾少女时的两项嗜好—网球及合唱。当时已届四十的她,不时代表台北西区参赛且屡获佳绩,我们姐妹中学时期遂有穿不完的球衣、球鞋,至于那各式奖杯则搁置窗台供猫儿饮水;合唱部分则一直唱到近八十岁无法久站舞台表演为止。狮子座的母亲非常享受团体生活,晚年的合唱团及教会是她的生活重心,常保童稚的她,在团体中总是受到欢迎照顾的,这是她的舒适圈,也是父亲离开后近二十年她找到的慰藉吧!
母亲从小就爱唱歌,在外婆制约下,她常借着放狗躲到野外引吭高歌,唱给稻浪、唱给河流听;有了自己的家后,终于可以放怀欢唱。她尤喜在做菜时唱,执锅铲等菜熟时唱的是抒情缓慢的歌,持菜刀剁肉便佐以《骑兵进行曲》;和父亲婚前通信时,分隔两地的他们,亦曾相约在某日某夜的同一时刻一起吟唱《霍夫曼船歌》,这是父亲临别前告诉我的。母亲事后获悉,大恸说,为什么不告诉她,她可以在父亲耳畔再唱给他听呀!
今年因《文学朱家》纪录片的拍摄,大姐翻出父亲一九四九年来台日记,也整出父母的往来书信。二十来岁年轻的他们,在该是情书的信件中谈的是文学、信仰,他们像护着火苗般护着心中对文学的信念,他们相信这会是彼此一生扶持守护最坚实的力量来源。之前他们仅匆匆见过三次面,就凭着如此鱼雁往返,母亲毅然离开医生世家的原生家庭,奔赴世俗眼中一无所有的军职父亲,大家口中我们的所谓“文学世家”是这么开始的。
她是因为我们姐妹仨、因为家务、因为经济而放弃纯粹的创作,选择相对轻松些的翻译工作吗?就像绝大多数的已婚女子面对家庭和理想必须取舍?她曾自封“后勤司令”,在父亲写作最盛、姐姐们办杂志出版社的时期,她选择在背后支撑,供养一屋老的少的拿笔的人;她永远慷慨,为友人随时可将存款提到个位数字;她热情,让周遭的人如沐春风;她像孩子,无心机得让人想照顾她;她像天使,让所有人都喜欢她,以世人的眼光她是至福至善的。
但当我重读书信、重新认识年轻的父母时,我好想念那至情至性、满怀文学信念的女孩。如果没有我们姐妹仨,如果当家境好转她选择的不是合唱、网球,如果她始终和父亲携手在文学的路上,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也终于明白二姐一直以来的鞭策,因为她始终没把母亲只当十全老人看待,母亲还该是和父亲初识时、那愿共负一轭的女孩。
母亲走前两个月查出肺腺癌,且已转移,一年前的X光片肺部并无任何征兆,应仍是和洗肾体力大衰有关,未想最终她和父亲竟罹患相同绝症,医院判断约莫就是端午前后吧!那时刚过完农历年,二姐为此安排了两天一夜的行程,携着以轮椅代步的母亲搭高铁南下高雄再转屏东,拜访父亲仅存渡海来台的结拜兄弟,也是和母亲最投缘、最能玩到一块儿、我们口中的大笃笃(叔叔),已然失智的大笃笃。看着生命已然倒数计时的母亲,以及已然初老的我们姐妹,久久、久久他喟叹说:“不像,都不像了。”他的比照图像是……三个毛丫头?那不顾一切奔赴父亲、热爱文学的女孩?
1967年农历新年,朱西甯携妻刘慕沙和三女儿返回妻子娘家看望亲人
在这告别之旅的路上,南下北上的高铁上,母亲没停地唱着歌,我们从小就听熟的歌,一如当时离家在高雄火车站站台等那只见过三次面的陆军中尉父亲来接她时,也如同最后转院在救护车上,乃至最后的那两个夜晚,即便已不成调,她躺卧病床仍未停止哼唱,这带给她快乐、带给她勇气的歌唱,陪伴了她一生。
原以为癌是母亲最后要面对的,但肾病仍抢在前,当所有血管已无法承受血液透析时,生命便已走到尽头了。于是在如守护天使般的家庭友人赵可式襄助下,母亲在荣总安宁病房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在那儿不再受医疗之苦,以安顿身心为主。母亲那三天得到最妥适最有尊严的照护,荣总安宁病房的所有医护人员,让我们姐妹终生感念。
母亲是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半离世的,临行前,当从国外赶回的大姐在病榻前轻唤她时,她微睁双眼,遂即闭目静听,以手紧握回应大姐的每一句话。身畔除了我们姐妹仨,还有她的至亲晚辈,在《奇异恩典》的吟唱中,一抹如云的影翳拂过脸庞,母亲溘然离去。
母亲遗容安然,即便没化妆,气色也好得不像洗肾患者。我们将她与父亲合葬于阳明山麓,以花葬的方式大化于天地,那四面环山的视野会是她爱的,天际盘桓的大冠鹫也是她爱的,与她至爱至亲的人长相厮守也是她最盼望的,这是我们姐妹仨仅能为她做的。
父亲
朱西甯(1926~1998),原名朱青海。当代作家,祖籍山东省临朐县。自幼爱好文学,虽身在军旅却能坚持写作,因而成为台湾军旅中出名的作家。代表作有《旱魃》《奔向太阳》等。
自晓事以来,父亲伏在案上笔耕的身影,是童年恒常的画面,也是此生无可磨灭的记忆。
是何时开始拜读父亲的著作,已难追寻,但清楚地知道,年少的我喜欢他的《狼》《铁浆》《旱魃》《破晓时分》这些以老家为背景的小说。那是一个亲切却也遥远的世界,读之热血沸腾、惊叹连连。但中后期的作品,除《八二三注》不这么贴近现实,其他书稿即便是小说,每每捧读都不禁脸红心跳隐隐抗拒着,是羞赧,是陌生,眼前至亲突然成了不认识的人。这是所有作家亲人不可免的尴尬吗?
此次《文学朱家》纪录片的拍摄,天文翻出父母的旧稿书信,有父亲年轻时的日记,有父母婚前的鱼雁往返。随着这许多文字出土,终能清楚看见他们,年老的父母,中壮的父母,以及年少的父母,他们的生命轨迹如此清楚地展现,恍如再一次活生生地重现。
朱西甯伏案写作
而其间始终不变的是,父亲对待文学的态度,虔诚力行在生命的每一时刻里。“用稿纸糊起来的家”原来不是传说,这个所谓“文学家族”的存在也非神话,以文学为媒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庭,自大家长起,念兹在兹的始终就只是文学,它已烙在每个家族成员的生命里。
父亲在和母亲的第一封信件中说道:“一切的事业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学不能平凡,因为文学不是换取生活的工具,文学乃是延长生命的永恒的灵魂之寄托。”他也曾写道天才是创作必要的,但孜孜不辍的书写更是重要。
年少时,看过多少才气纵横的书写者,之后为了种种原因,或求职或成家、或因为另类书写能更快更丰富地撷取所需而有不同的选择,文学创作本就是报酬低而缓慢又孤寂的路,它被放在第二第三……顺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坚持把它放在首要,甚至唯一的位置,就越发突显它的不容易。
全家合照。左起:朱天文、刘慕沙、朱天衣、朱西甯、朱天心
当眼前有诸多选择时,父亲坚持的永远是最不容易的创作之路。
父亲初来台时,曾婉拒当时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提携,坚持留守部队从基层干起。而后生怕影响创作持续,辞谢聂华苓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邀约(父亲是此计划台湾受邀第一人)。这些称不上快捷方式的可能选择,但凡对创作之路稍有干扰,全摒除在外。
父亲如此,姐姐如此,姐夫唐诺亦如是。这一路上,他们有太多赚大钱、得权势、广名声的机遇,甚至无须博取,但他们连被动接受都没考虑,理所当然地走着原本一直走着的路。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对大姐的创作描述成贵族式的书写,莞尔之余,不禁思索,何谓“贵族式的书写”?也许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不为生活而写,只写自己想写的。
说来容易,但首先要将生活所需减至极简,欲望降至最低,不为购房购车贷款所迫,不为卡债所扰,一家人守着仅有的一栋老屋甘之如饴地生活着。他们将所有的力气放在书写上,让生活成为笔耕的沃土,这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我是这样看着父亲生活的,也是这样看着姐姐们如此安身立命的。
父亲在创作《铁浆》《狼》时,正值我襁褓期,我曾多么庆幸没因自己的出生扰乱了他的笔。但近日听天心描述,板桥妇联一村时期,曾有那样一个夜晚,父亲伏案疾书,三岁的我因母亲不在身边嗷嗷啼哭,做姐姐的她生怕扰了父亲,恨不能捂住我灭口也好让父亲不受干扰。唉!若当时晓事,不等姐姐动手,我先就撞墙自我了断了。
而后迁至内湖,最记得的是,周末是父亲写稿日,周六半日休,父亲总写到隔日天明。周日早晨,母亲怕搅扰父亲补眠,总会带我们姐妹仨及一屋子狗至山边采野菜,直踅到近午才回家。吃过午饭,父亲继续伏案至深夜,若有客人来访,那么他入睡的时间会更迟。
朱家全家福
父母对友人满是好意,川流不息的客人是孩时生活底蕴,妇联一村时如此,内湖一村如此,后迁至景美亦如此。记得小学时期,每次疯玩到必须回家灌水时,总见客厅坐着站着满是人,在那烟雾缭绕的狭仄空间里,有我熟悉或陌生的叔伯阿姨们,他们常为我不太懂的话题喧腾争论。而母亲总在后面厨房忙,父亲则坐在沙发一隅,闲闲抽着烟,面前一切尽在眼底,但他是不是已神游到另一个世界,那无人可企及的世界?
那段时间,正是他创作畅旺时期,如他婉谢聂华苓邀约时所说的:“近一两年来,我是处于创作力的向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当然不仅是量,且是质的,历来我都不曾写过这么多的东西,而且有得心应手的感觉,特别是写一篇是一篇,篇篇可以出书,不似以往,出书的时候,十篇挑不出三四篇。这是主要的因素,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一生中并没有几年,这种清清楚楚自觉得出的黄金时期,我是一刻也不能错过。”
除了《破晓时分》《旱魃》,大家还在争论着所谓现代主义的同时,父亲早已着手并完成了《猫》《第一号隧道》《画梦记》《冶金者》及《现在几点钟》等无数长篇、短篇小说。
一九七二年,父亲尽早离开军职,专志写作,同年十月我们搬至景美辛亥隧道畔,入住初期,自来水尚未接通,整个小区只一两户人家。父亲维持夜间写稿的习惯,每天晏起,周末假日吃完中饭,父亲会随着我和二姐到邻家空房子踅踅,品头论足每家装潢隔间,拾些零星多余的砖瓦回去垫花盆,天气好时,则到周边山林探探。
那时方圆五公里除我们小区渺无人烟,也因此认识了两只圈养在山腰上供人拍戏的黄花大虎。又在一煤矿坑上缘废弃老屋前,移回两株至今已绿意成荫的金桂幼苗。还曾翻过一个山头,看见几个巨大球状槽,无人活动,只有大型槽车出入,我们脑补视作外星人基地,多年后也就知道它不过是个天然气工厂。而那段时间,我们享受着鲜少纯然的家庭生活,看似悠闲度日的父亲,白昼长篇小说、夜间短篇小说笔耕不歇地交出了六十余万字的《八二三注》,以及《非礼记》《蛇》。
后来姐姐们逐渐长成,也开始写作,并创办“三三”,家里恢复过往的热闹,只是出入的多是年轻的孩子,在一样喧腾的情境里,父亲仍端坐客厅一隅,晚辈学生有任何问题,都能找得着他。与此同时,父亲一样坚持着每天至少千字的写作,即便除夕夜一屋子年轻男女玩疯了,时间到了,他会静静隐没,再现身时,我们仨笑问他:“开笔了?”他总是眼神明亮地颔首,而他却从不这么要求我们姐妹。这段时间,他陆续出版了《春城无处不飞花》《将军与我》《春风不相识》《猎狐记》《将军令》……散文及论述文章还不在此列。
1976年留影。后排左起胡兰成、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
父亲晚年专心《华太平家传》的书写,曾两度易稿,第一次写至十多万字不满意重写,第二次写至三十万字却遭白蚁蛀蚀一空,再次提笔已是离世前十年,写至六十余万字,距离他原预估的两百万字还遥远。父亲会遗憾吗?在最后陪病的一晚,他和我说道《华太平家传》中,大美这一线故事的后续发展,即便因化疗体力衰弱,但仍神志清明地说了许多。这会是父亲至终的悬念?我无法确定,只知这是任谁都无法替代的,即便是他的同业两位姐姐都无法续笔的。
但若存着这一丝丝残念,父亲是不是会再次回到人世间,继续他喜欢的书写创作?而我们也因着同样对文学的虔诚与坚持,终将会再聚首。
若说信仰能让生命永恒、灵魂不灭,那么文学不就是如此?无论书写阅读,乃至生活态度,不都在突破生命的限制?心灵脑力极致开发,不正是信灵满溢般的至美?而文字的隽永不也是灵魂的不灭?父亲的身教与书写见证了这一切,而姐姐、姐夫的前行,让我无畏无惧,一样找着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何其有幸今生能与他们结伴同行,即便在这文学的国度里,我还做不到反馈,还只是个汲取者,但此生足矣。
人们总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父母的全貌、生命的所有,然父母意气风发的年少、风华正盛的青壮,孩子们多错过且无意追寻,这会无憾吗?因着父母留下的日记书信,让我为这《文学朱家》补上最后一块拼图,也如同他们在最终病榻上待我们仨陪伴、准备好才远行一般,让我们了无遗憾。
本文节选自
《桃树人家:读书人家的光阴》
作者: 朱天文 朱天心 朱天衣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 2021-11
编辑 | 朱皮特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