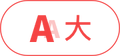本文来源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原题为《“预流”乃“古今学术之通义”——<叶显恩集>序》,作者为陈春声先生。

◉ 陈寅恪先生在所作《敦煌劫余录•序》提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学术。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
◉ 回顾学术史,人文学科的研究确有“预流”与“未入流”之别,而居于其间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在于学术的传承。
◉ 马克•布洛赫在其所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强调一位优秀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由古知今”和“由今知古”的素质,人类历史的研究者必须关注现实社会生活,掌握关于当今的知识以培养历史感,这样才能理解总体的历史,
◉ 要理解一位卓越学者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除了要认真研读其全部论著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尽量超越各种各样先入为主的世俗的成见,超越 “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的世俗的功利动机,超越日常生活中难免的世俗的追求和标准,真心诚意,将其置于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努力去理解作者“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才能真正学有所获。
“预流”乃“古今学术之通义”——《叶显恩集》序
陈春声
1984年底,叶显恩老师应约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作跋,近结尾处引用了陈寅恪先生1930年所作《敦煌劫余录•序》的一段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学术。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叶显恩老师自称“我虽无缘受业于傅老,承他之耳提面命,尚幸得为私淑而自足”。在跋文中,他这样阐发傅衣凌先生半个世纪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陈先生把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作为一个时代新学术的标准,亦即一个人的学术是否入流的标准,不愧为真知灼见之言。我觉得傅先生的可贵之处,也正于他能够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地发掘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当年叶显恩老师被傅先生赞誉为“治学严谨的中年学者”,卓尔超群,风华正茂。在中国学术界刚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许多新的学术方向仍在探索和寻求理解的背景之下,叶显恩老师引述前辈哲言,敏锐提出学术研究“预流”与否的问题,阐述的虽是傅衣凌先生工作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也可视为一种自况,表达了中国学术转型时期一位勇立潮头的优秀学者的理想与胸襟。陈寅恪先生当年在“预流”二字下面特别注明:“借用佛教初果之名”,也隐约地昭示着,后继者要达致这样的境界,是要兼具某种宗教感的。
叶老师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作跋的时候,笔者还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明清经济史研究室的一名硕士生。蒙老师错爱,常常有机会在各种场合向老师请教,也不时到老师家中聆听教诲,真的是获益良深。时隔30多年之后,再通读海南出版社编辑的《叶显恩集》书稿,更是深深感悟到,以叶显恩老师当年对傅衣凌先生的评价,回过头来理解和认识叶老师自己的学术,也是再恰如其分不过的。回顾学术史,人文学科的研究确有“预流”与“未入流”之别,而居于其间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在于学术的传承。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发展中,叶显恩老师那一辈的学者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叶显恩老师1962年从武汉大学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跟随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另一位重要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攻读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旅途。其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因地处岭南且得院系调整之赐,汇聚了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十数位卓越的人文学者,先生们读书问学,授业解惑,也在系内培植了那个年代颇为难得的某种学人间独有的文化氛围。在梁方仲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叶老师决定以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度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1965年8月,他与几位同学随同梁方仲教授做“北上学术之旅”,在北京向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吴晗、邓广铭、唐长孺等学界前辈讨教请益,同年10月独自取道曲阜、芜湖、合肥,前往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等地,做为期两个月的徽州历史文化田野考察。多年以后还经常被叶老师提起的这次学术旅行,不但奠定了本文集收录的成名著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的风格与根基,而且从根本上影响了这位当时就受到诸多前辈关爱和器重的年轻学者毕生的学术方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环境,应该是未曾亲历其境的后来者所难以臆想的。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常常会提到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的不公、对学术发展的压制、对国际学术交往的自我封闭。而事实上,那也是一个年轻读书人的头脑充满理想与憧憬的时代,不少年轻人受到时代感召,较少为“论资排辈”之类的思想所束缚,敢想敢干,从而超越了个人日常生活较为细微琐碎、计较利害得失的经验,怀着后辈所难以理解的情怀投身研究工作。对那一代青年学者来说,“不断地发掘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其实是带有某种不自觉的必然性的。问题在于,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还得讲究“家法”,必须“学有所本”。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人文学科的价值标准,更多地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正因为如此,在提倡大鸣大放和敢想敢说敢做的年代,一个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有志向的青年学者,能够受到名师教导,得到众多可谓“得一时之选”的前辈学者的指点与熏陶,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得以“传承”,从而避免像许多同辈人那样有意无意中坠入“野狐禅”之道,既是由于叶老师的真诚与睿智,更是一种造化。数十年后,叶老师接受访问时,对此仍念念不忘:“有幸得如此众多的名师指点,有幸亲睹他们的治学风采,不仅当时激动不已,今日念及依然有如沐春风之感。”
《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开始于20世纪初的“社会史大论战”关系密切。近100年前,让当年那批刚接受了欧洲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学者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与“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即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缓慢发展?为什么中国没有与欧洲同步,自主地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直至晚年,傅衣凌教授在授课时,还不止一次讲到自己年轻读书时,一直致力探求这个问题的思想历程。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学研究所谓“五朵金花”学术论争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社会史大论战”所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得以延续讨论,在新一代学者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启发下,兼具较多政治意涵的一次学术的“集体行动”。孕育和成长于这样的政治与学术环境,叶显恩老师的徽州研究,不可避免地利用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理论分析工具,受到那个时代中国史学界主流问题意识的影响。例如,他最早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和《关于徽州的佃仆制》三文,结语的最后一句阐述文章的问题指向与作者的学术期待,篇论文的表述几乎完全一致,分别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长期缓慢发展的特点,是有帮助的”,“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特别是长期缓慢发展的特点是有补益的”和“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特别是长期缓慢发展的特点,是有补益的”。由此细节不难看出,半个多世纪前“社会史大论战”提出的核心问题,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心中。这些论文较多地使用了“奴隶制”“农奴制的残余形态”“租佃关系”“定额租”“劳役地租制”“从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形态”“资本主义萌芽”等分析概念,从中可体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的讨论中,关于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诸多带有时代特质的问题影响之深。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关于明清徽州佃仆制度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叶显恩老师的工作已经展现了许多别开生面的特色。他1965年和1979年两次深入徽州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蒐集并利用了丰富的契约、谱牒、碑刻、诉讼辞状、财产簿册、档案、方志、文集等民间文书与地方文献,在研究中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所得口述资料的结合,注重相关典章制度的考证及其历史演变,注重个案研究及其与地域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工作明显地超越同时代的研究者,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这一从研究生学习阶段就得到梁方仲教授亲自指导的工作,也自然而然地带着前文提到的许多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做过奠基性贡献的卓越学者学术思想影响的痕迹,蕴含了学术传承应该“学有所本”的深刻哲理。
1983年《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出版,系统展现了叶显恩老师徽州研究的学术成就与思想创新,其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从“区域体系”的视角把握徽州社会的总体历史变迁。对这一工作的价值,叶老师自己有这样的判断:“就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地区做区域体系的分析研究,在国内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徽州研究的现代学术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藤井宏、傅衣凌等学者的工作,而1958年以后以契约文书为主的大量徽州历史文献的陆续发现,更使关于明清徽州商人、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宗族组织等问题的研究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将诸多具体的社会经济史问题置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的总体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则是从《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开始的。叶显恩老师自己表述了这一思想发展过程:“随着我对徽州地区历史资料掌握的增多,明清时期徽州农村社会的许多问题逐渐在我脑海中明晰起来,比如绪绅地主的强大、商业资本的发达、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宗族势力的强固、封建文化的发达、佃仆制的顽固残存等等。这些问题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对以上这些问题要作出合理解释,必须将他们置于徽州历史的总体中进行考察,并作区域体系的分析。我头脑中的这些问题在我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中进行了探讨,诸如徽州的历史地理、资源、土地、人口的变动、徽州人的由来及其素质等问题都曾涉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否理解“区域体系”视野的意义,是能否读懂这一学术著作的关键所在。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我们现在都知道,建基于“总体历史”观念的区域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最广者,首推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数代学者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学派的思想影响至今仍弥久而常新。叶显恩老师徽州研究“区域体系”视野的形成,也受到这一学派学术思想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建国后很长的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的,像法国年鉴学派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1977年,美国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来广州,197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黄宗智教授访问中山大学,向我介绍了这一学派的情况和美国学者从事区域性专题研究的情况,这样也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拓展关于徽州社会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正值欧美的各种学术思潮与中国学术界重新直接接触的时候,叶显恩老师敏锐地把握到其中具有“主流”意味的学术思想的启示,从而使建基于中国丰厚的历史文献分析和长期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工作,具有了更强的国际学术对话的禀赋与能力。这样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老师那一辈的成就,体现了“学有所本”与“叛师”的辩证统一,也超越了徽州研究这一课题本身的价值,具有了某种方法论上的意义,这就是学术的“预流”。
年鉴学派的奠基者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其不朽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道:“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也是徒劳无功的。”“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他强调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由古知今”和“由今知古”的素质,认为人类历史的研究者必须关注现实社会生活,掌握关于当今的知识以培养历史感,这样才能理解总体的历史,而“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叶显恩老师正是这样,他一直保持着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代社会变迁的专业敏感与学术热情,并与时俱进地发展新的学术方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叶老师就一直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气,直面各种疑虑,排除诸多困难,与一批同辈学者和年轻的学生一起,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拓展了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从1983年开始,他就与汤明檖教授共同担任“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的主持人,是为其时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同时推出的3个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重点项目之一。1987年他又筹划组织了傅衣凌教授担任大会主席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主编会议论文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这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外从事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众多一流的中青年学者,可谓得一时之选,且论文选题及立论都富于新意,至今三十余年,还常常被学界同仁提起,影响深远。2001年出版的《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集中反映了叶显恩老师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正如他在1987年的一次演讲中讲到的,这一学术兴趣的发展,除了得益于年鉴学派学术思想的启发,以及作为徽州研究学术实践的自然延伸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出于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区域性发展的学术敏感与关怀:“就中国而言,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现代化建设中允许各地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只有分别研究各个地区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这些特点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真正发挥历史研究对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作用。”这种敏感与关怀,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亦非削足适履的“硬套”,而是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历史整体性的学术思考为前提的:“以中国社会为例,面积几与欧洲相等的广袤国土上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个地区的人文社会情况又由于历史上本地区开发的先后、人口的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括全国历史的总体。”“历史的总体是由多系统网络复合构成的,一个局部地区只是总体的一部分,受总体的制约,与其它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全国性的综合研究自当以各地区的研究为基础,同样,地区性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狭窄的小天地,而必须放眼于全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把个别的局部的历史,无限推衍,描绘成普遍的历史,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但离开中国历史的整体,囿于一隅之见,孤立研究地方史,无疑也不能揭示历史的真谛。”这些在今日的学者看起来仍然兼具辩证逻辑与实践常识深度的道理,在30多年以前更是充满学术启迪的洞见,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判断,即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从历史学学科的本位上,真正理解30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学术发展的价值所在,感同身受地体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们当代关怀的精神实质及其意义。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体现“此时代之新学术”的学术探索,自然而然地因为其“预流”的特质“由附庸而成大国”。
进入21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之下,世界各地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交往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政府也适时提出了影响深远且反应热烈的“一带一路”倡议。面对这样的变化,具有当代关怀的中国历史学家首先要回答的,就是这一空前的“全球化”潮流的历史渊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诚如叶显恩老师所言:“16世纪(明中叶)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的时代;是建立殖民地和商业系统最活跃的时代;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西方冒险海商东来中国沿海寻找商机,并建立殖民地;由此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令人感佩的是,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叶老师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学术敏感,有计划地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海洋史研究上。本文集收录的多篇论述海上贸易、海上丝路、海洋文明、海岛文化与海外华人的文章,可以视为这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学家,壮心不已,努力追踪国际学术潮流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知道,这一努力还在继续之中,我们期待着老师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
学生辈对于叶显恩老师的感情与感谢,除了学问上入门的指点和学术思想的启迪外,还更多地表现在对老师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分享资源、奖掖后进的精神风范的感佩上。不管是受业门生还是私淑弟子,几乎所有被叶老师指导过的年青学人,都能感受到老师那份亲切、热情,以及细致入微、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笔者本人就一直得到老师的鼓励、关怀与指点,真的是没齿难忘。学界有不少同仁关注近20年“历史人类学”学术取向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我们这些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和欧美各地的十多位同辈学人能因缘际会走到一起,逐渐凝聚共识,形成所谓“华南研究”的学术群体,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近30年前就因叶老师而结识。或自己就是老师的学生,或到中山大学向老师请益,或受老师之邀到广州访问,或因老师绍介到外地求学,我们借助老师举办讲座、会议乃至家宴的机会,参加老师主持的各种合作项目,在老师大度包容、充满学术热情的推动之下,有意无意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共同的研究兴趣与学术追求。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许多像叶显恩老师这样的对中国学术发展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前辈学者的关心、扶持与指点,“华南研究”的同仁们才能说自己的工作是“学有所本”的,才敢于期待这样的工作“能够成为一个有着深远渊源和深厚积累的学术追求的一部分”。
叶显恩老师是在3年前就交代笔者要为这个文集做序的。当时不知深浅,自以为近40年来一直在老师的关心、指点下工作,不止一遍地读过老师所有的论著,完成这个任务应该不难,就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了。以后几次动笔,却发现要理解老师的学术思想,把握其内在脉络并非易事,加之行政事务繁杂,时时分心分神,结果就老是功败垂成。为了等待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序言,让老师的文集延迟出版,3年来老师虽偶有督促,但一直和风细雨,理解包容,任由学生交作业的期限一拖再拖。其中的温情与宽容,真的令学生感动并惭愧。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先生强调读书人要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首先自己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至理名言。笔者以为,要理解一位卓越学者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除了要认真研读其全部论著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尽量超越各种各样先入为主的世俗的成见,超越“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的世俗的功利动机,超越日常生活中难免的世俗的追求和标准,真心诚意,将其置于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努力去理解作者“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才能真正学有所获。在即将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笔者愿意提出这样的期待,与本文集的各位读者共勉。
是为序。
2018年7月31日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中
作者简介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