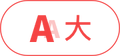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厦门大学出版社策划出一本书,请各位长期在厦大吃饭做事的老师写文章,现身说法,启迪后进。出版社的用心良善,然而,根据我们老祖先的标准,如欲启迪后进,须得有所谓“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贡献。我自揣没有这样的能耐,从小素无大志,现在依然胸无大志,“三立”皆空,何以启迪后进,怎么办?左思右想,还是遵照我们祖国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实话实说吧。
我出生在贫穷的农村,从小就深深体会到广阔天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辛酸生活。所以,虽然素无大志,却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小小志向:赶紧离开农村,换一个稍稍轻松而又可以吃上稳当饭的地方。这样的志向实在是很不堂皇高远,百分之百由“落后思想”产生出来的。可惜的是,怀有这种落后思想的人,无论是当时的火红年代,还是如今的金钱社会,恐怕都不止我一个。
既然一心想离开农村,就得处处寻找机会。屡屡碰壁之后,终于等到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最后一次时机。那个年代流行“走后门”,上选的招工名额和好大学,是万万不能有非分之想的。幸好在电影《南征北战》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会了国民党李军长的孙子兵法“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以自己世代贫农的背景,报名福州机电学校铸造专业、南昌地质学校和建阳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是不得已之选,那时的教师职业,大致介乎城市清洁工和农民之间,与贱业几希矣。至于地质和铸造专业,属于出大力、流大汗的行当,人弃吾取,或可乘机跳出农村。
1977年2月17日,即农历丙辰年除夕日,末班的邮递员送来了我的入学通知书:厦门大学!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事情。在身心俱泰、飘飘然之余,多方探听、苦苦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天上掉下来一个这么大的馅饼?最后归纳出二点:一是学校招生的老师,掖拔贫寒,天可怜见!二是这年学校分配给敝家乡6个名额,全部由善于走后门的干部子女入选,难免招来非议;稳妥之计,临时捉一个没有破绽的角色挡挡门面。我大概就成了这个挡门面的角色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之,农村是真的走出来了。既然进了名牌大学,下一步的如意算盘就比较好打了:刻苦三年,把大红封皮的毕业证书拿到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顺便再看看有没有不太识货的女郎,蒙她一个。这样就可以算是成家立业,安心为人民和自己服务了,端上一个比较平稳的饭碗。
不料世上之事往往人算不如天算。大学读了两年,学校招研究生缺乏生源,好心的系领导担心著名的导师没有生员报考,实在有失面子,于是,就动员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勉为其难前往充数。领导用心良苦,学生自应俯首效命。虽然明知是充数,但是交白卷总非好事。专业课的准备多少有点谱子,外国语却是连时下酒吧流行歌手朗朗上口的ABCD都不识半个字。权衡之下,似乎日本语中夹杂着许多汉字,或可蒙混过关。谋定而发,赶紧买了一本价格0.3元的日本语教科书来临时抱佛脚。歪打正着,张榜公布之日,同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居然成了孙山。这下子上大学时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大学本科文凭至今没有弄到手,更不要说那些识货和不识货的女郎了。
文凭和女郎全部落空,那就只好死心塌地读研究生吧。初次拜见导师,导师可是赫赫有名,不过似乎导师对我的最初印象并不佳:全身上下一片黝黑,里里外外依稀农民样,不像是“孺子可教”的样子。导师显然遇到了难题,如此田舍樗材,只能“因材施教”了。有一天,导师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比较熟悉,那就多多往乡下跑,寻找深藏在民间为一般图书馆所不经见的文献资料吧。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导师的话自然是要听的,十年下来,搜集的资料至今还用不完。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导师的先见之明。老实说,托世代为农祖先们的荫庇,那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勾当,还真是我的长项。否则,当年申报上学志愿,怎么敢如此奋勇地填上“地质”、“铸造”一类的专业?
如此随波逐流,居然在厦门大学又多混了几年。硕士、博士出身,总该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了吧?然而世运又不对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大学教师们最倒运的时候,所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我正当其冲,拖累得妻子孩儿一道受苦。穷则思变,学校里比较变通的学科,掀起了“创收”的热潮。偏偏我所赖于吃饭的专业,是可有可无、与世无补的“历史”学,半点变通创收的门道都没有。有些头脑活络的老师,跳出界外,改行从政、经商。唯有历史学科的人才,形同弃物,政商皆不要。行当不对,那就继续在学校里待下去吧。
要在学校里继续待下去,吃饭依然是个大问题。开源无门,那就节流吧。想当初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时候,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可以坚持半年不失体面。为何不把这种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带到学校里面来?主意已定,赶紧实行,果然节省了不少的银钱。正当洋洋自得的时候,有位领导前来劝诫:在校园里面背心短裤行走,于教书育人不甚协调。改进之道,背心改为T恤,就可于校风无碍了。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校园春光明媚,耍酷的后生小姐们,短裤越穿越短。如果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探索,我自信对下校园短裤的推广,多少有些开风气之先的贡献。
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吃饭穿衣的琐事;再说下去,有识之士不免要讥笑我格调低下。不过由于我素来缺乏大志,对吃饭穿衣的事情自然要格外的重视。读了古书之后,居然还知道古人有“吃饭穿衣即是人间伦理“、“吃饭穿衣即是道”、“衣食是佛”的大道理。如此说来,我耿耿于怀的吃饭穿衣问题,也就从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找到依据,可以于心无愧了。
我虽然素无大志,但知道吃饭穿衣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今托党和国家的洪福,衣食无忧。为了能够踏踏实实地吃饭穿衣,并且能够继续在学校里吃饭穿衣,我始终相信这样的道理:无论是哪个行当.只要是遇上了,就应当认认真真地做下去,力争做好。既然命运把我安排在历史学的这一行当上,我也只能横下心来,以不变应万变了。先学古文,再看古书,接着写些古人和今人大概都不会很喜欢看的古怪文章,美其名曰“学术论著”。如此持之以恒,十年过后,媳妇竟然很快熬成婆,套用前贤鲁迅先生的用语:“教授的饭碗摆在面前”。又十年过后,那就更加丰衣足食了。自己编撰的书籍,堆积起来足足有一人多高(这里要特别说明,自己主编了几套文献汇编之类的书,所以堆积起来如山),颇有点古人所谓“著作等身”的味道。道上的朋友看我踏实肯干,居然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给我戴上“著名学者”的帽子;隔三差五还给我送来好一些什么荣誉之类的封号。这些始料不及而又受之有愧的帽子、封号之属,自然都是身外之物,万不可当真自喜,不过同行朋友的好意,却也足以自慰与自儆:生活艰辛、衣食不易,不可一日有所懈怠。今后我还得一如既往地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做下去。
说来惭愧,最早告诉我“认真做事”这个道理的,是我那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村父母。所以,我至今依然十分怀念他们。
(收入陈支平著《随风摇曳校园间》,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2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