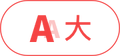我出生于农村,生长于农村,还在农村当了十多年的农民。1977年侥幸被送入厦门大学读书,一时洋气不起来。1979年考上硕士研究生,跟随傅衣凌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老师把我细细审视了一番,左看右看不像一个读书人,于是因材施教,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的生活比较熟悉,还是经常到农村去吧,或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就这样,我从1979年开始,就隔三岔五地往乡下跑,搜集民间文献与口碑资料等。其时还不知道有什么“田野调查”这样时髦的名字,学校和同学们查找我的行踪,都说“他到乡下去了”。虽然名称不甚堂皇,不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其时我的“往乡下跑”,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实行“田野调查”的先行冒失者之一,倒也有些名副其实。
经历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其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有些什么收获,我自己实在不好王婆卖瓜,然而不管是何种形式的“田野调查”,总是离不开从自己书斋走出去的衣食住行吧。从我的经历看,衣着的好坏洋土,似乎对于田野调查工作的影响不大,那时的农村,大概和我所研究的明清时期的农村,估计也差不多,破衣烂衫随处可见,农村的同胞们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大学里的读书人,随便怎么穿着,一定是没有什么可批判议论的。
讲讲“行路难”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交通之不便暂且不说,弄不好,还有被押进班房的危险。因此,在走出校门之前,头等大事是到学校的办公室开具若干张“学校介绍信”。其时中国的高校普遍穷困潦倒,请假出差的人员不多,学校办公室对于这些稀罕的出差人,很愿意提供帮助。我需要走几个县,他们就愿意帮你开具几张介绍信。如今的高校形同闹市,人多势众,车水马龙,每天需要出差的人络绎不绝,学校办公室就不能不显得位高权重起来。虽然说现在的教师出差,大部分并不需要到学校办公室开具30年前的那种介绍信,但是作为学校管辖之内的庶民,总不免有一些需要学校办公室盖一个公章的什么事情,那就十分麻烦,非得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由分管的副校长审批不可,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不说也罢。
口袋里装好“学校介绍信”之后,心里就踏实了。那时的厦门大学介绍信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威风。每到一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室的领导一看盖有大红图章的厦门大学介绍信,不敢怠慢,立即询问需要什么协助。我说明来意与需求之后,一般的情景是,办公室的领导在学校介绍信的背面,写上诸如“请县招待所、文化局、图书馆、档案馆、某某人民公社等予以接待办理”的字样。有了这些字样之后,我再一一到这些单位落实我所需要做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政府提倡科学、尊重知识,一时有“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感染之下,所到县及县以下的文化局、图书馆、档案馆、人民公社的领导们,对于我的到来,诚心欢迎,热诚相助。有不少干部还陪同我到乡下跋涉飘零。30多年过去了,这些干部的名字我也大多忘却了,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翻阅当时所搜集来的资料和重温我写过的所谓论著时,对于他们,心里总是泛起一丝隽永的温暖和谢意!
不过到了80年代中期,情景就有些不一样了,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渐显现出来。我到了县城,照例签转介绍信之后,县里的其他衙门,也照例会指配一两位干部陪同我下乡,陪同的干部也照样热情。但是到了公社、大队(后来改为乡、村)之后,热情的各级干部,照例是要请吃饭的。有饭岂能无酒?酒足饭饱之后,总得休闲一番。于是麻将一字排开,搓它几盘。我对麻将至今一窍不通,何况还有调查的任务,再加上学校请假的时日有限,我不得不婉转告诉热情的干部们,是否可以马上前往调查点?干部们悉心安慰,说是明天一早就去,耽误不了大事。我也只好耐心等待。第二天我早早起床,陪同的干部宿醉未醒、胃痛发作。健康第一,救人要紧,我反客为主,陪同前往医院。田野调查的事情暂时放到一旁。
虽然有过这样的挫折,但是过不了多久,交通逐渐便利,个人身份证也开始试用,从此以后,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就不需要经过学校介绍信和各地政府的签转及干部的陪同,变得独往独来起来。尽管如此,有些热心的、好奇的,以及警惕性高的当地干部,听说我来此地做田野调查,还是愿意陪同我一道前往。
田野调查的官场程序完成之后,接着紧要的事情,就是交通工具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地上风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据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还备受赞扬,并露脸全世界,而汽车一类的,则是难得一坐。如果调查点距离县城比较近,解决之道有二:一是依靠当地陪同干部的仗义,不知从哪里挪借一辆自行车一用;二是向当地修理自行车的店铺租用,一天的租金是一角钱。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比较偏僻的乡村公社食堂里,差不多是一顿饭的饭钱了。更要命的是这种租车费,学校是不能报销的。
如果调查点距离县城比较远,自行车有时也力所不及,那么就只能依靠国营的“班车”。“班车”的车费虽然比较贵,但是因为有国营盖红章的车票,回学校报销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麻烦之处是不能像自行车那样机动灵活,可进可退。当时的“班车”是稀有之物,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从县城到数十公里之外的调查点,无一例外是上午去、下午回,或者是即去即回。如果错过唯一的“班车”,就只能滞留他乡、寸步难行了。因应之道,或是事先在当地公社的衙门里,找好晚上落脚的场所,以便今天来,明天、后天或若干天后,按照“班车”规定的返程时间搭乘回县城;或是早上来,匆匆把事情做完之后,赶上下午“班车”返程的时间,回到县城。
不过计划的如意算盘也有落空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位书香门第型的同事一道前往一处偏僻的山村做田野调查,原本计划上午去,下午回。上午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当地的老者既热情又健谈,午饭让我们饱餐一顿,又帮我们搜集到不少资料。宾主气氛融洽,就不免有些忘乎所以起来。等到记起告辞赶到车站时,“班车”早已开走。要在这里过夜嘛,我的那位书香门第型的同事实在是没有与民同乐的勇气;再说,乡村的老者虽然热情,但是在当时大好形势之下,尚有某些“衣难蔽体”的贫困山村,他的家中实在也没有多余的床铺和棉被来让我们安顿。无奈之下,老者向我们指明了一条翻山越岭的道路,翻过眼前的这座山,就可以看到县城。“班车”须走坦途,绕了大圈,长达20公里;如果翻过此山,只存十余里的行程。
我成长在有中国华东脊梁之称的武夷山区,翻山越岭本来就是我的强项。既然有老者指明这样的近路通途,我就立刻告辞老者准备登程。可是我的那位书香门第型的同事,却是左右为难、畏畏缩缩。不走嘛,铁定就得在山村龟缩一夜;要走嘛,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最后禁不住我和老者的宣传鼓动,把红军长征的精神都搬出来,我的同事才勉强跟我上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回到了县城。这里顺便交代一句:为了让我的书香门第型的同事不扯后腿,我既当向导,又当挑夫。到了县城,我的同事颇有死里回生之感,庆幸之余,那天晚上的晚饭就由他请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