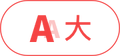谢湜,1981年10月生,广东澄海人。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香港孔子学院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广东历史地理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明清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在《历史研究》《文史》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其著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自第三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结业之后,我似乎就染上了一种瘾,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有时间,就非得把当地的古今方志找出一两本,或搜索一些史志文章,途中浏览一二。要是在当地刚好邂逅文本中提到的史迹,或听到当地人讲起某段似曾相识的历史记忆,就会兴奋不已,马上开始浮想联翩地串联历史线索了。
乡村调查的兴趣日渐浓厚,考察地点就从农村拓展到都市,乡村视角也从户外延伸到书斋,所关注的文献范围从民间文献联结到传世文献,从文本材料扩大到声音、建筑、仪式、景观等等,看到疑似碑状石块总要靠近多看几眼,看到任何景点的介绍铭牌就要问个究竟,乡间遇见一个老人家就总想去做访谈。一次旅行中,只要同行者中有几人染上这种“乡瘾”,就经常把一个短暂的观光游览随时变成一个历史人类学考察,接着就会打乱既有的游览计划,甚至因为停下来读碑、看谱、随机访谈而掉队,现场的讨论也很可能引来游客、当地乡亲好奇的围观。考察性质转变之后,“乡瘾者”们在实地、在车上、在饭桌上脸红耳赤的争论,通常会营造出某种特别的气场,在那些讨论氛围中,常识的误区和解释的纰漏、纸上谈兵和穿凿附会的危险也慢慢会被化解,重读文献乃至再访实地的热情也容易被激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观者、同行者很容易受到触动,引发学术共鸣,慢慢地也会被传染,成为下一个“乡瘾者”。
在2005年参加第三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之前,我有过几次实地调查初体验。第一次是2004年底随吴滔老师参加了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阮仪三、张雪敏等先生组织的瓜州运河申遗规划调研;第二次是2005年清明节与吴滔、佐藤仁史、太田出等老师赴江南嘉兴、湖州地区进行民俗调查;第三次是2005年6月下旬有奉加人科大卫、萧凤霞、葛剑雄、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陈春声、张侃等老师的队伍,参加温州、苏州调研。
在前两次的考察中,吴滔老师指导我结合扬州和苏州的县志、乡镇志的阅读,踏访实地,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也点燃了我从事江南研究的热情。在温州调研过程中,我每天跟随老师们在温州公藏机构查阅晚清民国的日记、笔记,在乡间阅读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们可以从族谱的片言只语中讨论很大的问题,而自己即便读了相关内容,也不知其所以然,于是问了很多完全不靠谱的问题,这让陈春声、刘志伟老师哭笑不得,也有点担心。于是,有天晚上他们和科大卫、赵世瑜等老师聊天时,喊我过去泡工夫茶,记得陈春声老师跟大家说:“谢湜好像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们看怎么教他。”其他老师一听,纷纷主动给我“补课”。其间,围绕如何让我听明白,他们彼此又有争论,拉锯了个把小时,更加莫衷一是。刘志伟老师只好叫停争论,“精辟”地总结:“谢湜我告诉你,老师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以为历史记载是那样的,其实,不是的。”当我们都等他接着展开阐述时,他说:“好了,讲完了。”于是,当晚的这场补课就在其他老师的哈哈大笑中结束了。回到房间后,我感觉很蒙,努力回味老师们的话,然而“悟禅”无果,经历了头脑风暴,觉得很累,只能倒头大睡。
随着考察的推进,特别是刘志伟老师途中的点拨,我开始有点感觉。刘老师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不是为了讲清楚某个道理,而是要通过各种文本的解读去理解历史的过程。”这番主张不讲道理的“道理”,对我十分重要,我慢慢开始改变自己读史料的方法,尝试去梳理史料,追述历史过程,而不急于归纳总结。我也渐渐明白了,在实地考察和访谈中深入阅读地方文献,是为了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大理解国家制度的实际运作。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及时的方法论纠偏。考察过程中,老师们非常生活化地谈论学术命题,也让我进一步体会到做学问的乐趣。当然,必须承认郑振满老师的“灵魂拷问”——“谢湜,你居然不会打‘升级’,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当时也让我备受打击。
有了这三次初体验,在北京师范大学开班式后,听张小军、黄国信、温春来、张侃、刘永华等老师的理论和实践讲座,感觉便亲切了些。学习了这些课程,我也意识到,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领域,牵涉到诸多复杂的学术史和理论问题,而民间文献的搜集和利用也绝非轻而易举。研修班同学间的交谈,则令我明白山外有山,必须永远秉持开放、谦逊的态度去理解更多的学术思想和流派,不能将历史人类学画地为牢。当时的住宿地点是校外的红星招待所,每天晚上回到房间,都没有热水。作为一个广东人,来到北京,直接体会到户外天气的干热和地下水的冰冷,每天临睡前都必须接受一场“冷静”的考验,大概也起到了消除浮躁的效果。
在北京上完三天的课程,研修班拔营赴河南济源。在长途火车上,不会打牌的苦恼涌上心头。好在几天时间里我早已和研修班同学梁勇、罗艳春、王大学、焦鹏各位仁兄建立起深厚友谊,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启蒙,鼓励我上桌实践。两副牌“升级”初试通过。这成为我本届研修班结业的一大收获,从此也在郑振满老师面前树立了“好笑”的形象。
初到济源,济续庙的历安足取令人霞撼,五岳四渎的神圣符号、唐代古墙的斑驳沧桑、宋代木构的巧夺天工,扑面而来。第三届研修班还没有形成后来研修班制作专门的田野文献读本的规范运作,我和大部分学员一样,被直接“丢”进聚落现场,从各种途径获取史料信息。在济渎庙阅读碑刻时,郑振满老师开始启发我们关注碑文中“老百姓的声音”,大家都觉得十分生动有趣。研修班晚上组织密集讨论,老师们期待颇高,但由于地方文献阅读不足,刚开始时,学员们要么围绕比较宽泛的方法论问题提出疑问,要么就某个实践的细节纠结不已,作为学员兼向导的李留文兄是研究济源的专家,但他一时也不知用什么方式将丰富的信息通过有效的方式引导我们的讨论,老师们都颇为着急。
第二天晚上,某段讨论环节触及田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这个时候科大卫老师忍不住挺身而出,把几位学员教训了一通。后来学员们回忆起这个细节,都觉得当时科老师就像手擎战斧的天神,飘浮在半空,一斧头一斧头地砍下来,让人不寒而栗,备受震撼。
其实,当晚科老师解决了我们很多人的疑惑。譬如,有同学认为,村里收集到的文献不一定真实,科老师笑着解释:我们学历史不是只追求一个唯一真实性,而是要看到多重的“真实性”,如果一块刻着文字的碑刻躺在你面前,你都不去承认存在一块碑刻这件真事,而首先是去质疑碑刻里记载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根本不用做实地调查,也就不能辩证地理解作为“真实”的虚假或虚构了。
还有同学觉得,大家一讨论就回到历史,联系现实不够紧密,没有关心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这下把科老师气得涨红了脸,他站起来辩驳:我们在田野考察时哪里是只关心历史,我们是在关心今天的中国,你要看到,在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们还在重复着几百年前的仪式,那是因为这些仪式对他们很重要,而我们要关心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得去理解他们为什么、怎么样遵守和举行这些古老的制度和仪式……在济源的考察中,我还注意到、老师们在乡间访谈时,经尝会关注当地乡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村民介绍了济源盛产花椒,而且大面积种植玉米用来喂牛的细节。这些访谈体验,对我后来自己从事乡村调查也是影响很大,我更加坚信,只有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才能理解历史。
在到达济源的第一次实地讨论中,研修班“校长”赵世瑜老师就跟我们介绍了卜永坚老师每次田野考察都随身携带旧方志,以及在庙宇中阅读碑刻时首先绘制空间分布图等先进经验。他和郑老师也反复提醒大家,要将实地所见所闻放入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研修班出发前,我恰好在电脑中下载了几部府志和县志,于是在济源宾馆里开始挑灯夜成,努力把方志里讲述的历史事件和地点简要记录在考察笔记中,白天到了现场就容易对应起来了。
在实地考察课程中,对沁水引水工程“五龙口”以及五龙引水各渠系沿线村落的考察,对我理解济源水利开发的社会过程帮助最大。8月3日下午,我们拜访了位于原利丰区灌区的梨林镇大许村,在村中二仙庙内访得一水册碑,碑阳为乾隆六年(1741)河内县派发的利丰二渠利地清册,碑阴锈刻有五龙口分水总图,按图索骥,乾隆二十六年(1761)《济源县志》的相关叙述的时空序列得以直观地呈现了,这让我兴奋不已。细读水册碑文,我还发现此类水利清册所代表的秩序化管理,并非限于一隅,其涉及的地域非常广阔。赵世瑜老师也悉心指点,指导我将乾隆时期沁水水利的发展置于清代晋、豫之间“泽潞商人”的贸易和活动中去理解。这对我启发非常大。我开始尝试突破一村一县一府范围,去思考济水、沁水水利开发背后更大的地域联系和社会机制。
在回程的大巴车上,我刚好跟卜永坚老师同座,遂请教一二,报告了我对济源水利开发时空序列的粗浅思考。卜老师对我的想法鼓励有加,“怂恿”我晚上参加圆桌讨论时就讲述这段历史。途中他又掏出方志,跟我讲述了方志中一桩官员间水利论争的趣事,对我启发很大。能一起在实地读同一部方志并产生共鸣,我顿时觉得十分激动。
当天傍晚回到宾馆,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几口饭,思维就已经完全沉浸在县志的记载和白天的见闻之中了。饭后我一边翻阅、抄录史料,一边走进讨论会场,坐下之后完全不知其他人在讨论什么问题。忽然卜老师在后排座位说:“我知道谢湜有很厉害的想法。”我被吓了一跳,结果主持人点名让我发言,我手心直冒汗,迟疑了几秒,才跟大家说,有点突然,没准备好,容我打开笔记试着讲讲。我展示了笔记本中一幅在途中草绘的流域示意图,然后开始结合方志史料和实地所见文献,讲述了宋代熙宁变法时期的济水水利开发,再到明代沁水水利开发和各渠系修筑的过程,接着对县域水利秩序和县际、府际水利纠纷进行了讨论。我隐约看到陈老师和赵老师点头肯定,卜老师也一直朝我微笑,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过关了。多年以来,我一直感怀卜老师的这次突袭推荐。
济源的实地考察是辛苦而愉快的,途中也是状况迭出,奇闻不断。首先是最为辛苦的研修班“校长”赵世瑜老师因为筹备会务劳累过度,忽然嗓子发炎“失声”,遂使他一路维持了敢怒不能言的“和蔼”形象。相反的是,晚上讨论时,科大卫老师几番战斧出动,外面就电闪雷鸣,而轮到郑振满老师点评,屋外就开始下雨,让人啧啧称奇。8月2日考察一山间道观,观内小院惊现“推动历史家人类,仙佛圣道在凡间”的对联,这一颇有见地且有趣的历史人类学“新解”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在学员们的怂恿之下,几位大佬在对联前合影留念。
第三届研修班结业后,我很快回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2005年秋季学期,我正好道修了邹逸麟先生的“河渠水利文献导读”课程,其间对水利共同体的问题颇有兴趣,遂阅读了相关理论文章。在请教了邹先生后,我将济源考察的心得进一步加工成为该课程的作业。在这篇习作中,我主要围绕明清时期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讨论县际行政、地方权势及两者的相互联系,如何对不同时期的引水技术、灌溉利益、农田开发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揭示16、17世纪豫北灌溉水利发展史中的制度转换和社会变迁。我认为,“水利共同体”的结构分析模式可能限制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空尺度,主张通过对地域拓展过程的动态考察,开阔华北水资源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思路。习作完成后,吴滔老师推荐我向《清史研究》投稿,后来有幸通过评审。在修订发表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老师惠予指正,令我受益匪浅。赵“校长”得知我的习作发表,也感到十分欣慰。
纵观过去十多年,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开创的富有特色的团野教学模式已开花结果。许多学校在实践教学和暑期学校中采纳或借鉴了这种模式。作为学员的我,后来也多次成为“田野与文献研习营:南中国海的历史与文化”“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等活动的田野导师。每次和更年轻的学员们在一起,我总会想起自己的济源之行,也更能理解他们的困惑、激情和感动。十多年来,我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同事以及海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同行们一起,继续推进历史学实践教学。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我也在努力思考,如何推进历史学处理地域时空及人地关系变迁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融合历史地理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建立基于中央档案与地方文献互鉴、文本解读与数据分析互联的框架,并充分考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综合影响以及在社会空间再生产中的能动性,关注跨地域人群流动的社会文化机制,拓展区域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问题。
2019年在飞机上看过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吻瘾者》。该片演绎了一场关于科学、信仰和爱情的思辨。时空交织二间,“吻瘾者”的寻觅和传递引发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专:我想,一代代的“乡瘾者”们乐此不疲地“走近传统乡村”“走进历史田野”“走向历史现场”,也许是某种学术趋势以及学科格局使然,但更多的只是顺从了求知者内心的追求。
2005年王屋山下的奇妙经历,让我彻底染上了“乡瘾”、在这片冀州之南、河阳之北的大地,愚公移山的传说流传了千百年。河曲智叟也是理性之人,但遇到移山成瘾的愚公,又听说邻人京城氏孀妻之遗男跳往助之,大概也只能慨叹瘾者皆愚,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