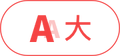由巫入礼的三条路径:从李泽厚“巫史传统”概念展开
曹元甲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巫史传统”是李泽厚提出的用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概念。作为一种理性化了的巫术传统,“巫史传统”的奠基与形成可以看作是由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平稳过渡的结果。由巫入礼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巫术文化外在仪式的理性化,一个是巫术文化内在心性的理性化。前者主要表现为周公的制礼作乐,后者集中表现为孔子的释礼归仁。由巫入礼从三条路径展开: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来看,巫术活动演变为礼乐活动;从文化仪式活动的主体来看,巫师蜕变为圣王;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指向来看,“神”转化为“德”。通过这一系列的转化,巫术文化过渡到了礼乐文化,神本主义思潮转向了人文主义思潮,“巫史传统”得以形成。这种转化并不是以断裂替换的方式发生的,而是以平滑过渡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在先秦时期便形成了一条文化延续性原则,该原则不仅规定着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向和演进模式,也制约着中国文化接受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筛选模式。正是由于“巫史传统”概念厚重的现实感以及浓厚的问题意识,它的提出不仅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反思贡献了一个极具启示价值的概念参照。
关键词:李泽厚; 巫史传统; 由巫入礼;礼乐文化; 圣王; 德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用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概念。这一概念直接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标示了出来。李泽厚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别,即在中国文化中,巫术传统并不像在西方文化中那样被彻底斩断,而是经过理性化之后渗透到了其他文化形态当中,继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文化并不强调至上神与造物主,反而注重人自身的地位,即便是国人相信的神也是由人而神、神人同质的。同时,中国文化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反而将生生不已的流变看作宇宙之本真状态。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均与巫术传统的绵延未断密切相关。对于巫术传统的延续方式,他认为,巫术的特质经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等手段和途径,“直接理性化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1)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0页。。正是基于此,李泽厚将巫史传统看作是“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2)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10页。。
所谓“巫史传统”,指的是理性化了的巫术传统,或者说是巫术的理性化传统,是巫术文化的精神内涵逐渐渗透到其他文化形态当中,从而形成的一种对其他文化形态始终起着举足轻重制约作用的文化传统。该传统可以看作是由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平稳过渡的结果,其形成过程漫长且复杂,既包括由巫入礼过程中外在仪式的理性化,也包括由巫入礼过程中内在心性的理性化。前一方面集中表现为周公的制礼作乐,后一方面重点表现为孔子的释礼归仁。经过周公、孔子等对巫术传统的转换性创造,巫史传统逐渐成型,无论是对后世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还是对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李泽厚本人在提出巫史传统概念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依然采取的是“六经注我”式的做法,所提出来的多为假说式的断定,在史料的编排和逻辑的论证上都比较疏阔,因而并没有对由巫入礼这一过程在逻辑上作详细的梳理。巫史传统概念提出之后,虽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对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着重研究巫史传统的几篇代表性论文(3)如刘悦笛:《巫的理性化、政治化和文明化——中国文明起源的“巫史传统”试探》,《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陆宽宽、冯昊青:《从“巫君合一”到“德政礼制”——论“巫史传统”的内在政治伦理逻辑》,《船山学刊》2018年第5期;金春峰:《“巫史传统”与中国哲学之我见》,《中国文化》2022年第2期。,也没有将焦点集中在阐释和发挥巫史传统的形成历程上。由此,本文力图在尊重和遵从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和《“说巫史传统”补》等文原意的前提下,从由巫入礼的三条路径,即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文化仪式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化仪式活动的指向,对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化机制作细化展开和分析,以期揭示出隐藏在中国文化脉络当中并始终制约着中国文化演进方式的连续性原则,进而凸显出巫史传统概念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从巫术活动到礼乐活动
由巫入礼首先表现为文化仪式活动性质的转变,即由巫术活动向礼乐活动的转变。由于巫术文化和礼乐文化并不是一套纯观念系统,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操作性的实践系统,因此,从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化就可以看作是由巫术活动向礼乐活动的转化。从逻辑上来说,在回答巫术活动如何转化为礼乐活动之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巫术活动为什么要转变为礼乐活动?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可能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巫术活动的式微问题。对此,学术界有几种说法,如保存历史经验说、预测天象历数说和领导军事战争说。李泽厚持最后一种观点,他说:“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表现出来。因为任何情感(喜怒)的干预,任何迷信的观念,任何非理性的主宰,都可以立竿见影地顷刻覆灭,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作为领导、负责军事行动的‘巫’‘君’,其从事的‘巫术礼仪’自然不能不受到这一方面经验教训的制约影响,从而使原巫术活动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消减,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增强,使各种神秘的情感、感知和认识日益取得理性化的解说方向。战争经验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4)李泽厚:《从巫到礼释礼归仁》,第20-21页。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战争确实可以导致非理性的巫术活动趋向解体,但它只能解释巫术文化为什么会衰落以及巫术活动为什么会式微,而无法很好地解释巫术文化衰落或巫术活动式微之后为什么不转化为其他的文化形态(如哲学和宗教)或其他的活动形式,而只能转化为礼乐文化或礼乐活动。
事实上,礼乐活动也并不是一种纯粹理性化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活动,并且仪式繁琐。如果这一转变是由频繁而又残酷的战争导致的,那么代替巫术活动的就应该是一种理性色彩浓厚且剔除了繁文缛节的活动形态,而不可能是礼乐活动。因此,领导军事战争说只可能是导致巫术活动解体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巫术活动转向礼乐活动的主导性原因。导致上古中国从巫术活动转向礼乐活动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某种外在性力量,而是传统的强大惯性力。因为,如果是外在力量的强行介入改变了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那么,前后两种文化形态在演化脉络上一定是断裂的,在存在样态上一定是不连续的。比如,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导致西方中世纪文化代替古罗马文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替代或文化覆盖。反观上古中国,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化在时间上要漫长得多,在程度上要缓和得多,且二者在演化脉络上基本上一脉相承。因此可以推断,推动中国从巫术文化转向礼乐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内生的传统惯性,而且这一传统惯性力量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就已形成,经过上千年的巩固和强化,在轴心时代的先秦时期便成为一条隐蔽的连续性原则,始终贯穿在之后的中国历史当中。由于上古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西方早期文化中的那种彼岸性的超越世界,因此判断和取舍一种文化的标准就不可能是彼岸性的超越标准,而只能是一种此岸性的现世标准。在这种此岸性的现世标准里,未来由于其未来性使得古人不可能发展出一种进步的线性历史观,于是只能以过去与传统作为标准来衡量和损益自身的文化形态,甚至一种文化越是古老,越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历史观和文化观,作为文化母体和源头的巫术文化在上古中国获得了一种不可撼动的神圣性,并一脉相承地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当中。以世界文明为背景来审视中国文明,我们常常会惊叹于其强大的连续性,由于这种连续性,中国文明可以历经几千年的风云激荡而延续至今没有间断。相比那些历史悠久但中途不幸湮灭的文明来说,不能不说连续性极强的中国文明是一种奇观。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这种连续性原则在上古中国由巫术文化到礼乐文化过渡期间就已经形成,从而成为文化传承与转化的主导性力量。正是在这种主导性力量的作用下,上古中国巫术文化就很难演化为纯观念的,并且具有外在超越特征的文化形态,如哲学和宗教,而是会以体匿性存的方式转化到一种与之同构的仪式活动即礼乐活动中。
现在的问题是,巫术活动如何转化为礼乐活动?一般来说,原始巫术是非日常进行的特殊性的活动,而礼乐活动则是上古时期人群生活的日常规范,因此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作如下问法:非日常的特殊性活动是如何转化为一种日常的社会规范活动?或者说经过“绝地天通”一度被统治阶级垄断了的巫术活动,是如何转化为一种被多数人尤其是社会上层人普遍遵循、履行的活动?这二者是如何具体衔接和过渡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李泽厚在《说巫史传统》中给出了一些猜测性的论断。他认为,从巫术活动过渡到礼乐活动的关键环节是“祭”。“‘祭’的体制的确立是这个转换性的创造核心。……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仪制)。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5)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1页。。他还征引现代民族学的研究结论以及民俗学、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来佐证由巫到礼是以“祭”为中介而进行的。
关于殷人这种至上神与祖先神合一的神的观念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王国维认为,帝喾即是殷人的祖先,“为商人所自出帝,故商人谛之”(6)王国维:《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王国维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6页。。徐复观说:“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受祖先神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祖先作中介人。周人的情形,也同此。”(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5页。陈梦家说:“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模,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8)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62页。张光直认为,“商”字的含义即是祖先崇拜(9)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95页。。在商人那里,神的世界和祖先的世界几乎是共享的同一个世界,二者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祖先生为人、死为神,无论生死都保卫着本氏族、本部落的成员。“人与神、人世与神界、人的事功与神的业绩直接相连、休戚相关和浑然一体。……生与死、人与神的界限始终没有截然划开,而毋宁是连贯一气,相互作用着的”(10)李泽厚:《说巫史传统》,第8页。。而围绕着祖先神的祭祀仪式,便是“礼”的开始。《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通过“祭”,“原始人的巫术活动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图腾崇拜和禁忌法则,开始演变成一套确定的仪式制度,它由上而下日益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人群必须遵守的规范制度”(11)李泽厚:《说巫史传统》,第52-53页。。总的说来,由巫术活动到礼乐活动的整个转化机制的秘密就在于将神人化和将人神化。这里的“人”就是指祖先。将神人(祖先)化的结果就是洗掉了巫术活动中的非理性以及神秘性色彩,将人(祖先)神化的结果就是将巫术中洗掉的神秘色彩和情感性因素重新注入到平凡的日常祭祖活动中,从而赋予了这些日常的祭祖活动庄严肃穆的神圣威严感。《礼记·祭统》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可见,礼乐这种文化仪式活动并不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而是仍然保留着巫所特有的那种与天地沟通、与鬼神交往的神秘力量,尽管已经世俗化和理性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将礼乐称作礼教和乐教,这里的“教”既有宗教之义,也有教化之义,既是世俗的又同时具有超世俗性,既是亲切的又是神圣的,既保留着对于神明的那种敬、诚、畏的心态,又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不使其越出理智的范围。“于是我们就在此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远古巫术的衰落,而另一方面,又是远古巫术所包括的内容的发扬光大”(12)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术崇拜及相关问题》,转引自李泽厚:《说巫史传统》,第56页。。衰落了的是带有时代特征的具体内容,而发扬光大下来的是寄居于这种具体内容之中的灵魂。
尽管礼乐文化和巫术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在中国,这种转变并不是新文化形态对旧文化形态的彻底抛弃,而是一种在延续和传承中的平稳过渡。后面的文化形态里仍然带有前者深刻的烙印,甚至可以说,后者只是前者通过自我更新以另一种面目的亮相。理性的觉醒并没有使巫性智慧边缘化,相反,这种巫性因素巧妙地渗透进伦理当中,从而使得伦理学也巫性化了;同样,巫术文化也巧妙地吸收了理性的和形而上的因素从而伦理学化了。正是这种和顺平稳的发展方式使得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像古希腊时期那样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尖锐冲突的现象。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式具体表现为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接受,而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否定中吸收。这是一种平稳的、和缓的、渐变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的演进模式遵循的是一种连续性原则,从而造就了世界上唯一的没有间断的文明。文化人类学家一致认为,巫术文化是文化之源头,是孕育其他文化形态的母体,任何一个民族在其早期都经历过一段极为漫长的巫术文化时期,但到了“轴心时代”,大多数民族都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突破”现象,即剪断了与巫术文化的脐带,进而演化出一种或几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在古希腊,经过几百年的诗、哲之争,巫术文化逐渐解体,孕育出了哲学、科学和宗教等文化形态。巫术中的理性因素为哲学、科学所继承,而非理性因素则为宗教所吸收。相比之下会发现,巫术文化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完全解体,而是采取了一种体匿性存的方式,继续存在于礼乐文化当中,因此在中国也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将理性与情感割裂开来的现象,而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与理交融在一起。李泽厚指出,“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与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中国则由‘巫’而‘史’,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13)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1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中西文明体是在同一个起点上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二者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在中西文化史上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该“事件”的理解,巫史传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概念视角。
二、从巫师到圣王
随着巫术活动向礼乐活动的转化,巫术活动的主体也逐渐转化为礼乐活动的主体,即由巫师转为圣王。由巫师到圣王的转变是一个时间上极为漫长,而且程序上又十分复杂的过程。如果将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简化一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两个分界点:一是颛顼的绝地天通,二是周公的人文革命。前者使巫、圣合一成为可能,后者让由巫到圣过渡成功。
《国语·楚语下》有一段记载: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4)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141-1149页。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上古时期,民神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神不杂、民神异业,只有巫师可以往来于神人、天地之间,这个阶段是灾祸不至、求用不匮的理想社会;第二个阶段是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人人都可以祭祀降神,也就是所谓的“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其结果是民渎神、神狎人,社会财货匮乏,灾祸不断;第三个阶段是颛顼命南正重、火正黎区分民神,绝地天通之后,又恢复到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状态。这段话还透露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颛顼绝地天通后,通神的权力收归圣王,圣王垄断了通神权,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老百姓不再拥有通神的资格,“家为巫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巫术文化由盛而衰的重要标志,也从此开启了数千年巫王合一、政教不分的历史。
圣王地位的上升同时伴随着巫师地位整体上的下降。古史的记载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巫师的社会地位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转变。不过,颛顼绝地天通之后,尽管巫术文化从整体上转向衰落,但个别巫师的地位却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比如在殷商时期,当时最大的巫师就是君王,在《论语》、《国语》、《墨子》、《荀子》以及《太平御览》等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记载作为大巫的商汤王做牺牲祈祷上帝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在殷商时期,巫、王不仅是合一的,而且王是首巫即最高的巫师。陈梦家就说过:“王者自己虽然是政治领袖,仍为群巫首。”(15)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在神本主义思潮笼罩整个社会的前提下,一切智慧、力量皆来源于上帝神和祖先神,作为世俗政治的最高首领,君王想要获得统治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就必须占有这种智慧和力量。在颛顼绝地天通之前,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种智慧和力量,但是为了垄断这种智慧和力量,统治者切断了其他人与上天相交通的渠道,并将这种资格占为己有。这样,神权便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普遍认为君王就是首巫。张光直说:“如果重新审视三代开国君王的丰功伟绩,我们会发现这些功绩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力大无穷可力挽狂澜,他的步法即所谓‘禹步’,是后世巫觋所用的一种特定步法。如我们所见,商汤可祭祀祈雨,后稷具有使庄稼长得更丰盛更快速的特殊才能。这些传统信仰得到了商代甲骨文的印证,这也说明帝王确为巫觋之首。”(16)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刘静、乌鲁木加甫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40页。苏秉琦说:“在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那个阶段上,玉器成了最初的王权象征物……神权由王权垄断,一些玉器又成为通天的神器。”(17)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9页。李泽厚说:“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18)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7页。也就是说,以颛顼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通过绝地天通等一系列活动,逐渐垄断了神权,使得原本各司其职的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这便是上古时期由巫到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
由巫到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西周时期。在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且极为坚固,学界普遍认为,该传统肇始于西周时期,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贵族对殷商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个结果。近百年来,学者们通过对大量的考古资料的研究发现,殷商是一个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的王朝,神本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殷商时期。占卜、祭神行为极为频繁,人殉、人牲现象层出不穷。武王翦商之后,为了吸取殷商王朝快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周人重新审视人与人以及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处处反商道而行:废除人牲、人殉制度;将“天”拟人化,将合德与否作为赋予或转移天命的标准;将商人的“帝”拉下神坛,同时又将圣人送上神坛。废人牲、人殉是把人当人,体现出来的是人道主义;把天拟人化是把神当人,体现出来的是理性态度;将圣人送上神坛是把人当神,体现出来的是超越精神。人道主义、理性态度、超越精神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西周以降,人文精神绵延不绝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人对传统文化曾经发起的一场人文革命。
当然,任何文化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绵延了无数个世纪的神本主义思潮具有强大的惯性,即便是在鼓吹、提倡人文主义的周王朝,这种思潮也依然强劲。事实上,周朝的巫风确实很炽烈,这从周原遗址出土的大量卜骨中可以得到证明,史料中的记载也可佐证这一点。比如在《尚书·洪范》中就记载了周灭商后,武王特意拜访商朝遗民箕子,请教卜筮之道。可见,在周初,龟筮在决疑中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这种信仰底下,周人渐渐萌发出了一种对鬼神的怀疑精神。《尚书·大诰》说:“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由此可以看到周人对占卜的不信任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周人现实、理性的一面。在现实和卜筮的博弈中,周人不像殷人那样对鬼神无条件服从了,理性精神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种考量。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宗教意识也逐渐理性化为伦理意识,宗教性的“帝”逐渐为伦理性的“天”所取代,沟通鬼神的巫师也逐渐为替天行道的圣王所取代。正是这一人文革命使得由巫到圣的转变成为可能。
与巫、圣之间的不同相比,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似乎更为重要,因为这才是整个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地方,也是我们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理论视域。虽然周初时期的君王已经有了伦理意识的觉醒,但这种伦理意识仍然与鬼神意识混合粘连在一起,没有完全区分开来,因而其身份与职能常常表现出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形态。也即是说一个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的头领既是政治领袖,也是道德楷模,同时还是最大的巫师。“圣(聖),通也,从耳”(《说文解字》),“从耳”即闻天道,而口则发号施令。可见闻天道、发号令的人既是圣人,也是王者,“圣”即内通神明,“王”则外治百姓,这便就是“内圣外王”的真正来源。正如《易传》所描述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些对圣王的描述其实完全可以换成对巫师的描述;《易传》中还有“神以知来,藏以知往”、“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等等对圣王的描述,无不可以看作对巫师的描述。从巫师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划出了一条由接通神明的巫师到参天地赞化育的圣王的平滑轨迹。
由于从巫到圣之间的转化是一种平滑过渡,因此在巫师和圣王这两种身份当中存在着诸多重叠之处。确切地说,在巫师转化为圣王之际,巫师的宗教功能并没有消失,而是为圣王所继承和吸收了。如果将西方一神教作为参照系会发现,中国文化当中确实没有超验意义上的唯一神或至上神,自然也就没有对唯一神或至上神的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他神灵的排他性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世俗性的实用主义文化,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在中国文化当中,并不存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天国与人间清晰的领域划分,也不存在教会和君王分别掌管天国教权和世俗政权的权力结构划分,而是表现为一种教权逐渐被理性化并为政权所接手,但同时仍然具有神圣性的政教合一式的权力结构。与伊斯兰文化那种政权依附于教权的政教合一权力结构相比,中国文化的政教合一表现得更加理性化和人间化。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虽然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界限清晰的“两个世界”,而是表现为李泽厚所说的“一个世界”,但这“一个世界”也并没有陷入一种无价值支撑的纯事实状态,反而是蕴含着一种超越性和神圣性的维度,而这种维度的存在恰恰是源于巫术传统的被转化性创造。正是在这一强大政教合一传统的影响下,后世的权力结构往往是一种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结构,君王既掌握着政权,同时也是天意的代理人和道德的表率者。既然君王乃道德之表率,于是君王就被赋予了神圣性的使命,成了在道德上对自身严苛要求的圣王;既然君王承接着天意,也就意味着他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从历代君王对灾异、祥瑞的态度以及频频下“罪己昭”的行为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都可以追溯到巫史传统这一文化源头那里去。
三、从“神”到“德”
从仪式活动的指向上着眼,由“神”到“德”的转变也是由巫入礼的一个关键环节。在巫术文化中,巫师是最有威望的人,因为他能通神;在伦理文化中,圣王是最受尊崇的人,因为他最有德。现在的问题是,巫术活动中的“神”与礼乐活动中的“德”之间是否也存在继承关系?如果存在,二者之间又是如何转化的?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考证一下“德”字的含义。郭沫若说:“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彝铭中……都明白有德字出现。”(19)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1页。后来的古文字学家多不同意郭氏的看法,认为德字在甲骨文中早就有了。如徐中舒就认为甲骨文中的“”字应为德字的初文。对于“德”字,陈来解释为:
这个字(徝)从彳从直。金文中在这个字下面加“心”,成为“德”字。另外,金文中也有无彳,而从直从心的,作“惪”。《说文》心部:“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广韵·德韵》:“德,德行,惪,古文。”(20)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77页。
德最初只与人的行为有关,而加了心部之后,则又与人的意识联系起来。这样德就有了德行和德性两个方面的含义。这就是说,德既是一种外在行为,也是一种内心状态。从直从彳就是直走、循着直线走,不要走弯路;从直从心就是将心摆正放直,也可以解释为循着自己的本心行动。郭沫若考证出:“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徝(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21)郭沫若:《青铜时代》,第22页。无论是循着外在的直线标准,还是循着内心的正直标准,都有循着、遵循、顺从的意思。容庚就认为“徝”与“循”近(22)求是:《经史杂考三则》,《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4期。。《庄子·大宗师》中有“以德为循”的说法。李泽厚也认为,“‘德’正是由此‘循行’的功能、规范义而为实体性能义,最终变为心性要求义的”(23)李泽厚:《说巫史传统》,第68页。。甲骨文的“德”字中有双大眼睛,可以推测这双大眼睛很可能是神的眼睛。《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之所以“戒惧”、之所以“不敢易纪律”就是因为那双大眼睛盯着,所以“德”有被注视的意思。闻一多将“徝”解释为“示行而视之之意”(24)求是:《经史杂考三则》。。
高田忠周说:“悳,从直从心。又直训正见也,从十从目从,者隐也,十目所视,匿者不能逃也。”(25)转引自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2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第990页。这里的“十目所视”就是众目睽睽了。从解释为神的眼睛和解释为众人的眼睛,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宗教观念,后者就是伦理观念了。《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贡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明君子是常常出于众目睽睽之下的,任何过失都逃不脱众人的注视。《说文·彳部》:“德,升也。”段玉裁注:“升当作登。《辵部》:‘迁,登也。’此当同之……今俗谓用力徙前曰德,古语也。”桂馥义证:“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成语“从善如登”即是“德”字此义之沿用。
综合以上诸说,“德”可以理解为,在神或众人的注视或监视下,君王始终听从良心的召唤或者遵循正直的标准小心翼翼地谨慎行事,并且奋斗不止、自强不息。从上述推断中可以发现,这种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因为它还不是人自觉追求的东西,而是一种带有很强他律性色彩的禁忌系统。这种禁忌色彩就是从巫术文化的母胎里带过来的。李泽厚就说:“‘德’作何解,众说不一。我以为,它大概最先与献身牺牲以祭祖的巫术有关,是巫师所具有的神奇品质,继而转化为‘各氏族的习惯法规’。所谓‘习惯法规’,也就是由来久远的原始巫术礼仪的系统规范。‘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周初讲的‘德’,处在第二个阶段上,‘德’在那里指的是君王的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行为,而主要是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26)李泽厚:《从巫到礼释礼归仁》,第21-22页。从上述各家对德字的解释来看,李泽厚的“德”义三部曲解释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从《周书》中保存有大量的关于“敬德”、“明德”的论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
周公曰:“……则皇自敬德。”(《无逸》)
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召诰》)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召诰》)
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召诰》)
克慎明德。(《文侯之命》)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多方》)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多士》)
自成汤至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
克明德慎罚。(《康诰》)
虽然敬德、明德均是指德的彰显,但从“敬”与“明”这两种对德的态度能看出二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敬”透露出主体与“德”在地位上的不平等,二者之间是存在一定距离的,此时的“德”还带有某种禁忌色彩,还属于一种人的异己的产物;“明”则透露出二者在地位上显得较为对等了,而且距离也近了许多,这时的“德”就已经是人开始自觉接近和追求的东西了。在周初,“敬”和“明”还纠缠在一起没有完全分开,表明周人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完全摆脱巫术观念的束缚。正是这两种观念的纠缠粘连使得周人对于德常常表现出含混不清甚至矛盾的态度。郭沫若也意识到了周人这种矛盾的态度,只是他将这种矛盾态度解释为周人对“天”的两面性策略,并认为这是周统治者有意识的“神道设教”,是一种愚民政策(27)郭沫若:《青铜时代》,第20页。。从前述的分析来看,情况也许并非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周人道德观念与巫术观念的粘连,并不是出于统治者自觉的政治策略,而是二者在当时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正是这种模糊粘连,才导致了他们对于德的这种模棱两可、矛盾暧昧的态度。周人这种对伦理的宗教态度在《诗经》中也能看到,如《大雅·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由此可以发现,在巫术文化中的“神”与伦理文化中的“德”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过渡关系,它们在基本精神上高度一致。
虽然“德”已经将“神”作了理性化的处理,但从中仍能看到“神”的影子,仍能感觉到附着其上的神秘气味。卡西尔在比较自然宗教和伦理宗教时说:
禁忌体系强加给人无数的责任和义务,但所有的这些责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完全是消极的,它们不包含任何积极的理想。……因为支配着禁忌体系的正是恐惧,而恐惧唯一知道的是如何去禁止,而不是如何去指导。……然而,人类伟大的宗教导师们发现了另一种冲动,靠着这种冲动,从此以后人的生活被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肯定的力量,一种不是禁忌而是激励和追求的力量。(28)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38-139页。
尽管卡西尔谈的是两种宗教类型的对比,但对于中国巫术文化和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大体适用。只是在上古中国巫术文化式微之后,并不是像西方那样靠宗教(伦理宗教)插手来突破闷得透不过气来的禁忌体系,而是以血缘为纽带,靠着“将神人(祖先)化”再“将人(祖先)神化”的程序来打破原来巫术文化中禁忌体系,并进而将其一步步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人格。这样既冲淡了巫术文化中非理性色彩浓重的人格神的强制性特征,又得到了以血缘为根据建立起来的等级秩序(礼)的保证,从而使得解除了禁忌体系之后的社会并没有成为一盘散沙,而是遵循延续性原则,在礼乐制度的维持下平稳缓慢地向前滑行。这是中国文化极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正如童恩正所言:“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说,没有巫师集体的‘制礼作乐’,就可能没有现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谓的带有‘中国特征’的古代社会。”(29)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术崇拜及相关问题》,转引自李泽厚:《说巫史传统》,第55页。
如果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对由巫入礼过程中外在仪式的理性化,那么孔子的释礼归仁则是对由巫入礼过程中内在心性的理性化;如果说孔子之前的“德”还带有强烈禁忌色彩和巫术意味,那么到了孔子这里,其禁忌色彩逐渐褪去,巫术意味也逐渐消散。春秋时期,随着礼乐文化的逐渐衰微,礼当中蕴含着的神性因素逐渐流失,礼最终变成了一具徒有形式的僵硬外壳。孔子看重的是礼所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是礼背后所蕴含着的理念和精神。如果礼仪不体现某种精神价值,那么宁简勿奢,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既反对巫术礼仪,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也反对为礼仪而礼仪,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于是他以“仁”释“礼”,将人的情感注入礼仪当中,使礼成为情感表达的恰当方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与“礼”相比,“仁”更为根本,只有建立在“仁”之上的“礼”、只有表现了“仁”的“礼”才是活生生的“礼”,否则就成了束缚人的繁文缛节,即便强行遵守,也只能导致虚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对质疑三年通丧的学生宰我说:“今女安,则为之。”(《论语·阳货》)这里“心安”就是一种不仁的情感状态。当一个人麻木不仁时,“礼”对他来说就成了没有意义的符号,甚至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负。在由“神”到“德”的转化过程中,孔子采取的并不是去神归仁的激进方式,而是借由“礼”这一中介,通过释礼归仁的温和转换,不仅赋予了“礼”以情感内容,同时也改变了“礼自外作”的历史传统,使得作为“通德”的仁爱情感具有了贯通天地的超越维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礼乐文化,并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历史建构。也就是说,在孔子释礼归仁的同时并没有否认礼乐文化与巫术文化之间的联系,因此当子贡问道:“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道:“吾有占而七十当,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又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马王堆帛书·要》)从孔子对巫术占卜的态度,既可以看出他对待巫术文化鲜明的理性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礼乐文化与巫术文化之间连续性关系的承认。
正是“德”与“神”之间存在着的连续性关系,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带有强烈的宗教性色彩,使得“道德”本身带有浓厚的“超道德”意味,进而也使得许多“局外人”对中国哲学产生误解和曲解,甚至就连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在评价孔子和《论语》时都很难切中肯綮。关于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和内在超越性特征,国内不少学者诸如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民等人都注意到了,并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阐发和论证。唐君毅和牟宗三认为宗教性特征内在于中国文化之中,超越与内在、人文与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体两面;而徐复观则认为,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现象,而非本质性要素,随着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演进,这种宗教性特征终究会被扬弃掉(30)李明辉:《儒家人文主义与宗教》,《宗教与哲学》2014年第3期。。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牟宗三、唐君毅二人与徐复观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但他们都一致承认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和内在超越性特征。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他们都只是给出了事实性的描述,没有给出产生这一现象的理由,即都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具备如此特征,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巫史传统或许就是一个颇有解释效力的理论视域。
余论:“巫史传统”概念的文化价值及学术意义
巫史传统是巫术文化通过体匿性存的方式被吸收到礼乐文化当中,进而形成的一种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由巫入礼是巫史传统得以形成的关键环节。前面我们分别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本身、文化仪式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化仪式活动的指向三条路径,对由巫入礼的过程进行了多维度的展开与描述,立体化地呈现了巫史传统得以形成的运行机制。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来说,巫术文化活动逐渐转变为礼乐文化活动,但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巫术文化的精神内核,这就使得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生活的世俗性礼乐制度仍然可以与天地相通且具有神圣的宗教性。比如《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同时,也使得作为一种内在的人性情感的仁具有了通达宇宙天地的超越维度;相应地,达到了万物一体仁者境界之人,也可以参与到宇宙大化的流行当中。从文化仪式活动的主体来说,通达鬼神的巫师变成了参天地、赞化育的圣王。所谓圣王,既包括外王也包括内圣,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圣王既是政治领袖,也是道德表率,同时还是宗教先知。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指向上来说,巫术活动指向的“神”转变为礼乐活动所指向的“德”。这里的“德”既有世俗的社会性道德的一面,也有超越的宗教性道德的一面,从而使得礼乐活动所指向的道德极具弹性,是一种超道德的道德。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世俗的宗教性特征,还是内在心性的超越性特征,无论是道德的超道德特征,还是权力结构的巫王合一、政教合一特征,无不受到巫史传统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巫史传统的提出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价值的概念参照。
巫史传统也是我们研究李泽厚本人思想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课题。刘再复就认为,在李泽厚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文化命题中,“最重要的是‘巫史传统’这一命题”(31)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李泽厚自己也说:“我以前曾提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感本体’、‘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一个世界’等概念来话说中国文化思想,今天则拟用‘巫史传统’一词统摄之,因为上述我以之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概念,其根源在此处。”(32)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1页。李泽厚为什么会把巫史传统作为统摄他所提出的其他描述中国文化特征概念的根本性概念呢?先看“一个世界”概念。在李泽厚看来,所谓的“两个世界”并不仅仅指存在着两个并列的世界,更关键的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尽管在巫术文化中人与鬼神杂然相处,俨然两个世界,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不仅神可以影响人,在一定程度上人也可以干预神、取悦神甚至借助某种技术手段操控神,从而为自己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秉持的是“一个世界”的世界观,而这一文化特征直接可以追溯到“巫史传统”。“实用理性”同样与巫史传统息息相关。由于巫史传统所导致的“一个世界”框架的限定,理性只能是出自历史的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产生于历史,历史是理性之母”(33)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9页。,因此这里的理性不可能是脱离生活、历史、经验、人生的先验理性,而是“作为现实生活的‘工具’”(3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39页。。但实用理性又不同于西方的实用主义。“由于巫史传统,尽管一方面强调‘用’即‘体’,‘过程’即‘实在’,工夫即本体,勿需发展出对象化的存在设定(客观性的人格神或物质世界或自然规律the law of nature),也勿需发展出一套主观的逻辑范畴即先验理性,从而有与实用主义契合相通处;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个‘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仍然设立了虽由人道上升却要求‘普遍必然’的‘客观’天道(而不像实用主义者从不设定这些客体对象),以作为自己行为的信仰和情感的依托”(35)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40页。。因而,实用理性并没有变成一种工具主义,这同样是巫史传统塑造后的产物。再以“乐感文化”概念为例作一点分析。“乐感文化”当中的“乐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乐感”,而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神秘体验,而这种体验与巫师通神过程中所获得的神秘体验一脉相承,却与宗教意义上的神秘体验大相径庭。用李泽厚的话来说,“由于巫史传统,通天人的神秘经验未采取基督教神宠天恩的人格神方式,而以主观‘境界’即心理(仁、诚、德、本心、良知呈现等)方式来展现其超出认识、超出理性、也超出一般经验的宗教性格”(36)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16-117页。,因此,“它很难是如Kant那样的道德的神学,而只能是非理性的审美的神学”(3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17页。。正是由此,李泽厚提出了与西方宗教“罪感文化”相对立的审美“乐感文化”概念。通过巫史传统可以解释的李氏文化命题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分析。笔者只是试图说明,在李泽厚的思想当中,巫史传统命题占据着统摄性地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更能彰显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体系的一贯性和系统性。
除此之外,巫史传统概念的提出对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建构也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由于巫史传统的绵延不绝以及其强大的影响力,任何试图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都需要经受这一传统的筛选和过滤。由于巫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一元化的超验信仰实体,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学习和吸收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并不会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倾向,因此,由巫史传统延续下来的中国文化乃是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之一,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都会被吸收进来,但这种吸收仍然是有条件的,即凡与该传统在根本原则、根本特征上不相符合的文化会被损益与扬弃,要么被改造,要么就直接被拒之门外了。这里的根本特征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包括内在的超越性、道德的超道德性、世俗的宗教性以及政教的合一性等。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一次是东汉末期佛教文化的输入,一次是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输入。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照单全收了佛教文化,而是根据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则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改造和筛选。本来是秉持“两个世界”具有出世特征的佛教文化,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变成了一种带有宗教性的世俗文化,禅宗就是这一改造和筛选的典型产物。对于禅宗,很难说它是纯粹的宗教还是纯粹的哲学,事实上,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带有宗教性色彩的哲学。“担水砍柴,无非妙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这些禅宗式的话头无不表现出那种既内在又不失超越性、既在世又不失出世性的中国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和巫史传统的潜在影响密不可分。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潮水一般涌进中国,但大多数思潮和主义在热闹了一阵后便烟消云散了,而唯独马克思主义为国人所接受,并持续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除了一些现实原因之外,文化传统的制约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自主选择的因素,但这种自主选择的背后始终有传统文化的制约和筛选机制在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不是一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超验性世界,而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的带有理想性的可能性世界,体现出来就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现实性特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中国,而且在道德领域也试图为国人提供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现出来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特征;而这种道德由于与共产主义理想连在一起,因而又体现出一种超道德的特征。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巫史传统的影子。因此,如果忽视传统所具有的制约和筛选机制,就不仅会遮蔽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也会阻碍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个大问题,在这里只能一笔带过。在此提及只是想说,无论是外来文化的引进还是本土理论的建构,无不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当然,笔者并不是在主张传统决定论,而是说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巫史传统,无论是在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方面,还是对本土文化的建构方面,都发挥着极其强大的制约和筛选作用。不管对其赋予何种价值判断,不管对其持肯定态度还是持批判态度,都不得不面对它,不得不以概念的形式将其提炼出来,使其从一种民族集体潜意识变成我们可以审视和反思的意识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转化性创造,这正是李泽厚提出巫史传统概念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黄文红 / 微信编辑: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