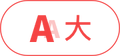作者简介

张 越(196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执行编委,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北京市教学名师。出版学术专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评论等130余篇。
感谢作者授权推送。本文发表于《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1期。
★
郭沫若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什么?
——以民国时期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作用的人, 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是一个群体, 是经过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在1949 年之后又聚集了更大范围的史学家致力于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术现象, 但是,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代表性人物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 对郭沫若史学成就和影响的评价多种多样, 其中, 实事求是的评价有之, 沿袭旧说、与事实不甚相符、过分夸大的评价也时有出现, 还有许多是那些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而蓄意负评郭沫若的, 以及那些不了解事实、不明就里、人云亦云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和谩骂。在一定程度上说, 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关乎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 对郭沫若史学评价出现的问题, 一定程度地也反映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中出现的问题。尽管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不能完全等同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 但是其中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郭沫若带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 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 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试以民国时期郭沫若史学受到的各种评价为主要材料, 意在重现郭沫若史学建树在当时学术界所引起的各种反响, 借以说明郭沫若史学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带来的贡献及其他, 希望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评价郭沫若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3 月,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 “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标志, 是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 此说已成学界公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时, 国内正值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潮时期, 言及郭沫若此著, 一般都会联系到社会史论战, 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也确实影响到了社会史论战:正是1929 年出版的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1930 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将问题引入中国社会史领域, 论战也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转入了中国社会史问题, 影响到了论战的走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主要观点, 受到动力派的激烈批评, 也成为《读书杂志》中的论战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 郭沫若著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社会史论战有没有直接的关系?郭沫若是不是专为论战而著此书, 还是出于别的原因撰著此书并出版后与论战不期而遇?对此, 学术界也存在争议 。从实际情形看, 首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完成的, 因为远离国内论战中心, 对论战的了解并不全面;其次,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对于正在开展的社会史论战只字未提, 书中将商周史置于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框架中、提出的西周为奴隶社会等, 都成为社会史论战中被重点批评或攻击的内容, 却也未见郭沫若直接回应 (仅对陶希圣有过简单批评) 。这都使我们对于该书与社会史论战的关系产生疑问, 这至少可以提示我们, 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社会史论战完全绑定在一起解读是不够全面的。
说到底,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历史著作。作为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的历史著作, 其著述动因必然与当时的史学状况有着直接关系。20 世纪初, 梁启超倡导建立中国的“新史学”, 其主旨之一, 就是希望对旧史学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算, 参照西方史学, 融入史学“求真”“科学”的历史学等现代因素, 建立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的“新史学”。到了“五四”前后, 不同于古代史学的近代中国史学, 无论是在历史观点、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机制、人才培养、历史教学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垣、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等人, 都为此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当时的情况大致是, 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 使上古史的研究获得了明显进展, 亦因“二重证据法”而凸显了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胡适借乾嘉考据的研究方式阐发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也受到了广泛关注。顾颉刚通过对史料的考辨, 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陈垣的“古教四考”、《元西域人华化考》 (上) 等名著也已完成问世。重视史料和考证, 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大约同一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日渐高涨的过程中, 胡适提出“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的文化纲领, 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整理国故”运动随之兴起, 后果之一, 便是将学术研究趋势引入了对“国故”的“部勒”“理董”、整理和考证中。事实上, 民国时期以历史考证为主流史学趋势, 即与新史料的运用、“科学方法”的提倡以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有着直接关系。
郭沫若对“整理国故”运动并不赞成。1924年郭沫若就说:“大凡一种提倡, 成为了群众意识之后, 每每有石玉杂糅, 珠目淆混的倾向。整理国故的流风, 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写出版, 是在“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 特别是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 是郭沫若采取的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否定行为, 也是他努力开拓中国史学发展新途径的尝试。此为撰述《中国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直接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 郭沫若表达了他对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特点的判断。第一, 肯定王国维、罗振玉“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 有着“近代的科学内容”, “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 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 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第二, 质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 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 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 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可见, 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等人的研究是“近代式的”, 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当“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 而继续发展的途径, 并非是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 《中国哲学史大纲》也不是典范。在郭沫若看来, 须用“批判”来取代胡适的“整理”, 理由是:“‘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 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 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必经的一步, 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这里, 郭沫若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批判”式的史学意向, 而要达到“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的目标, “整理国故”是难以胜任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述意图, 正是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 超越“整理国故”。
再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书过程来看, 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后, 在接下来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文中, 将该时代定为“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 初步尝试将商周史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框架中, 同时也深感材料上的欠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研究方法上的错误:“对我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了”, “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 毫无讳言, 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 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根据的资料, 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 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 而且……还影响到方法。”这样, 他开始将精力放到研读甲骨文和金文上来, 据此写出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 (该篇原题为 《周金文中的社会史观》) 两篇。在此期间, 根据对古文字的研究心得和前面将唯物史观结合于商周史的思考, 他又写就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成为使用唯物史观系统阐述中国历史阶段性发展的最早的篇章, 发表于1928 年上海《思想》杂志第四期, 在有意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时, 该篇文章“作时的目的原无心作为本书之导论, 以其性质相近, 故收于此”, 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导论”部分。
从上文郭沫若本人正面阐明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述动机和该书成书过程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几点认识:首先, 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否有与社会史论战相关的或其他“难写出的” (见原书“解题”) 原因, 因材料不充分而难有定论, 然而作者在“自序”中充分表达的著述意图却十分明确, 就是要在王国维等开辟的“近代式的”中国史学的“出发点”基础上, 抵制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批判”取代胡适对“国故”的“整理”, 揭橥用唯物史观“清算过往社会”的历史研究新路径。这一著述意图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其次,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各篇的完成, 展现出了从具体研究到一般研究 (从“社会生活”到“古代社会”、从“社会变革”到“社会史观”、从商周时代的社会到“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并且不断有意识地克服“公式化”的逻辑过程 (从对资料的怀疑到研读甲骨和铭文、从自省“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到不断修正书中的观点) , 这些特征对于一个新出现的史学思潮的继续发展, 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学术意义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伊始, 除了在社会史论战中引发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外, 就有人从该书学术价值的角度作了评论。如嵇文甫在1931 年10 月12 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的书评说:“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看, 他那独创的精神, 崭新的见解, 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 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 自值得我们的敬仰。”次年的1 月4 日, 《大公报》再发张荫麟的书评:“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二文不约而同地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新史学开其先路”“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 可谓一语中的。社会史论战结束后,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影响持续发酵。1937年何干之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 开了一个新纪元”。《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 几层摸着了一些儿边际”, 而顾颉刚在1947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则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 自有此书后, 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1949年齐思和撰文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同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很快发展起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近代中国史学最重要意义当是“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 这条“大道”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纪元”。
二、“创通知例开拓阃奥之功”: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
近年来批评郭沫若史学的声音, 大都指责郭沫若是把“五种生产方式”的教条硬套在中国历史上的代表,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顾历史学的“求真”属性而刻意追求历史学“致用”特点的始作俑者, 是只重理论不重史料和史实的典型。限于篇幅, 本文对此暂不一一辨析, 只是想说明, 郭沫若史学真的是只重理论、不重史料的“空中楼阁”吗?一个现象是, 一些批评郭沫若史学的观点, 大都抓住并刻意放大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教条化、公式化的不足, 却少有提及郭沫若在释读古文字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运用古文字材料对上古史的研究成绩、对先秦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被一些人所“憧憬”的民国时期学术氛围中的一些著名学者, 却对郭沫若古文字研究的贡献极为重视并予以高度评价。
郭沫若先后完成出版了 《甲骨文字研究》2 卷 (1931年) 、《卜辞通纂》1 卷、考释3 卷、索引1 卷 (1933 年) 、《殷契余论》 (1933 年) 、《古代铭刻汇考》 (1933 年)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1934 年) 、《殷契粹编》2 册、考释3 册 (1937 年) 等专门著作。在金文研究方面, 他完成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931 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2 卷 (1932 年出版, 该书在1934-1935 年间增订为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二书) 、《金文丛考》 (1932 年) 等书。这些著作, 在对卜辞和殷周青铜器的研究方法、对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解读、对甲骨和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获得了民国时期史家广泛肯定, 如唐兰总结甲骨学研究的状况说:“卜辞研究, 自雪堂导夫先路, 观堂继以考史, 彦堂区其时代, 鼎堂发其辞例, 固已极一时之盛。”顾颉刚等著《当代中国史学》称:“王 (国维) 氏死后, 在甲骨文字研究上, 能继承他的, 是郭沫若先生。”“全盘整理存世铜器铭文而为之总结的, 有郭沫若先生及吴其昌先生二人。”李亚农在其1941 年出版的《金文研究》一书的“跋”中写道:“本书所徵引的学说, 差不多都出自郭鼎堂先生。鼎堂是著者的同乡前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规模之宏伟, 在中国金文学史上, 诚所谓迈古迢今。一千年来, 金文学家辛勤研究的成果, 不消说是摄取在大系之中的, 而鼎堂自身创获之丰, 又有远迈前人者在。”
在民国时期, 即使是那些对郭沫若在唯物史观史学方面的成就持异议的人, 或者是那些不赞同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人, 也都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研究成绩表示由衷的钦佩。比较典型的就是在政治立场和学术理念上与唯物史观史学完全对立的傅斯年。1930 年, 对新史料研究极为重视的傅斯年, 看到郭沫若在日本完成的《甲骨文字研究》后, 希望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分期发表, 然后再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中的一种单独出版, 而且稿酬从优。此事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做成, 却可见傅斯年对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的充分重视。1947 年, 时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 特意以通讯方式提名推举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 在“被提名人资格之说明”中, 傅斯年评价郭沫若对两周金文研究有“创通知例开拓阃奥之功”, 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分别排比、尤能自成体系”。院士候选人的推荐者需要列出被推荐者的三部代表性著作并作评价, 傅斯年列出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评价“此书集两周青铜器铭文有年代及国别可征者三百余器, 详加考释, 附以图录, 创为南北二系之说, 为研究古金文者一大进程”;列出《金文丛考》, 评价“此为大系之姊妹篇, 以青铜器铭文为资料, 释其文字并讨论其含义与经史纪录比较互证, 尤多卓见, 为研究古代思想及社会史最注意原始资料之作”;列出《卜辞通纂》, 评价“此书选传世卜辞之菁粹者凡八百片, 分类排列, 比珈释词, 创见极多, 为研究殷墟卜辞一最有系统之作”。1948 年4 月1 日, 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第一届81 名院士的名单, 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 (人文组) 院士。
由于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以及不同的学术理念, 傅斯年不可能认同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成就,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上提名他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也恰因如此, 傅斯年却能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因素, 专从学术角度给予郭沫若在古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以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 并提名他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这不仅说明郭沫若在该领域的成就得到公认, 也说明了傅斯年评价郭沫若所表现出的学术态度和学者品格, 近几十年来, 愈来愈多的人关注并从事于对傅斯年学术的研究, 那么, 对于傅斯年推荐郭沫若为院士的所作所为, 似乎也应该予以关注并有所借鉴。
需要明确的是, 郭沫若并非仅仅是为了研究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 他目的是通过释读古文字史料, 去证实他的古代社会研究, 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知其所以然”。郭沫若说:“余之研究卜辞, 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 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一步, 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 与社会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 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 尤舍此而莫由。”这层意思, 民国时期的学者也看到了。如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郭沫若是代表社会思想的人物, 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不得不清算中国以往的中国社会史, 要明了中国社会史的全部, 不得不先明了中国社会的起源——古代, 要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 不得不研究甲骨文字, 走到了罗振玉、王国维的路上。”“这是郭先生继罗王研究甲骨文字道路, 是一个矛盾, 是一个辩证的发展。总之, 郭先生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最有成绩的人, 也是研究甲骨文字最有成绩的人。不止开中国史学界的新纪元, 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也有莫大的贡献。”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也说, 郭沫若研究殷周古文“乃藉以考证古代社会史, 而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基础也”。他进一步认为,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虽承罗王二家之后, 无大精萃;然其治此学之目的, 在以证古代社会, 其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实足为中国古史开一新纪元也。”[齐思和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研究的仅限于殷周, 而每篇又依据极明确的史料。而且他不但依据书本上的资料, 又因为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甲骨金文, 将卜辞金文用到社会史研究。”从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角度而言, 正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和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上下了功夫, 使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显得罕有其匹;从古文字研究领域而言, 则是将新材料有效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的范例。
对于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 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两大趋向来认识。此说若以粗线条观之并无不妥, 毕竟近代中国史学存在将史学中的“史料”与“史观”分别“演绎”至极致的表现, 言及“史料”, 即有“史学便是史料学”口号, 论及“史观”, 也有“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 往古代的公式上套”的现象。但是, 若将二者视为泾渭分明、此消彼长的关系, 却也未必尽然。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看, 作为“史观派”大宗, 其开创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在研读了甲骨文金文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其开创者郭沫若位列“甲骨四堂”之一, 凭藉在古文字方面的史料建树, 郭沫若忝列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列。因此, 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认定为绝对意义上的“史观派”并不准确, 评价郭沫若也要从他在“史观”与“史料”的多重建树中客观为之。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 曾引用王国维在为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写的“序”中所发“于创通知例、开拓阃奥, 慨乎其未有闻”的感慨 ,来说明古文字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傅斯年在推荐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说明书”中亦用“创通知例开拓阃奥之功”来评价郭沫若在两周金文研究的成绩。这里, 同样用“创通知例开拓阃奥之功”来概括郭沫若在甲骨及金文等古文字方面的建树, 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 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创通知例、开拓阃奥”,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重视史料的传统, 史料和考证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之一。
三、郭沫若的先秦诸子研究
思想史是抗战时期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家开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侯外庐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政治与经济, 集中于社会形态分析, 尚无暇顾及思想学术史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需求以及抗战时期重庆当时的状况, 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扩展到思想学术史领域有了可能。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 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民国时期郭沫若在先秦诸子方面的研究亦有重要贡献, 成果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部著作中。1945 年二书分别结集出版后, 很快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介绍与评论文章纷纷见诸报刊。1946年, 《图书季刊》新第7 卷第1、2 期合刊中将《十批判书》置该期推介的42 部学术著作的首部进行介绍:“郭君是书之价值, 在对先秦诸子作一种新试探, 以求对诸子有比较真确之认识。又重新估定诸子价值, 如对墨子之估价, 与梁启超胡适诸氏所见异趣。其谓荀子可谓杂家, 谓韩非之思想以现代眼光看, 不能谓为真正之法治思想, 皆与晚近一般推论不同。吕不韦秦王政一文抉出战国末期思想及政治上之隐微, 是为书中最精辟之一篇。”
1947 年1 月4 日《大公报》的《图书周刊》第1 期发表朱自清的评介《十批判书》的文章 (文章署名佩弦) 说:“十篇批判, 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 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我推荐给关心中国文化的人们, 请他们都读一读这一部《十批判书》”。朱自清还结合当时古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来评价《十批判书》, 在对冯友兰曾经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说中的“释古”之意作了一番阐发后, 认为“释古”就是“客观的解释古代”, 然而“无论怎样客观, 总不能脱离现代人的立场”。朱自清强调并肯定了《十批判书》中“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和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指导这两大特色, 遂凸显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独到之处, 朱自清的观点也与上述郭沫若的自我评价多相吻合。
1947 年4 月5 日的《大公报》上又发表有对《十批判书》的“侧重于批评”的评论文章, 不过该文仍然认为“通观全书, 创辟的见解甚多, 虽也不少证据不足, 近于武断之处, 然而证据凿确, 精审不移之见解更多。著者本是文学家, 所以文笔极其流畅, 虽是考据文字, 而生动活泼, 引人入胜, 尤属不可多得”。
与上述评论观点相左的是齐思和的评论。齐思和在他任主编的《燕京学报》第30 期 (1946 年6 月出版) “书评”栏目中写道:“郭氏本为天才文人, 其治文字学与史学, 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 创获固多, 偏宕处亦不少, 盖其天才超迈, 想象力如天马行空, 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齐思和的结论是:“此书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 若以哲学眼光观之, 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 思想之密。”“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 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 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 二氏书之价值, 世已有定评, 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 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 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也有争议。譬如, 华岗在1945 年写就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认为:“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书》中, 又大做翻案文章, 特别攻击墨家, 而赞扬儒家, 因此有人说郭沫若成了抑墨扬儒论者。其论据既甚牵强, 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郭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家, 又是我所景仰的革命战士, 但是他在历史翻案工作中, 常常以出奇制胜, 而不以正确致胜, 我却期期以为不可。”而吕振羽在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修订版 (1946 年) 则说:“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出版后, 其中并有不少牵涉到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和本书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许多主要论点。我一面衷心钦佩郭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 一面感谢他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 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 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 深入的去检讨一遍。”
此外, 《燕京学报》第32 期 (1947 年6 月) 还发表了容媛写的《青铜时代》的书评, 文章介绍了《青铜时代》的主要内容后说:“以上所举为其荦荦大者, 可见郭先生想像力之强, 时作推陈出新的见解, 更兼文笔流畅, 一气呵成, 大有引人入胜之感。”
以上的评论, 以肯定性意见为主, 表现在对郭沫若在两书中的新见解和流畅的文笔等的赞誉。批评意见以齐思和为代表, 主要质疑其在书中表现出的文学家式的想象力有悖于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严谨的逻辑论证的原则。华岗则对书中过多的翻案文章、论据牵强而以出奇制胜的做法不满。容媛评《青铜时代》“可见郭先生想象力之强”也暗含此意。
对先秦诸子的研究, 属思想史研究范畴, 除了细心考索材料外, 研究者的史学观念、基本立场、著述动机等主观因素有着更多的发挥余地, 成就“翻案文章”的机会或许也更大些。不消说, 郭沫若在40 年代转而对先秦诸子进行研究, 其主观意图十分明显。即如他所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 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历史, 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适应度”, 这样明显的主观愿望当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研究者的客观立场。郭沫若对先秦学术思想及有关人物的评价有着自己的标准, “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然而过分地强调“人民本位”的标准去判断历史人物的“善”与“恶”, 并仅以善恶、好坏来代替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都有着绝对化的偏颇。如果再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而对先秦诸子的思想及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于现实中, 难免就会与专从学术视角进行考察评估的结果发生矛盾。
综上, 通过时人对郭沫若史学的各种评论, 在帮助我们了解和考察郭沫若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什么之外, 还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明了郭沫若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既要明确郭沫若带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的或潜在的各种影响, 也不应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教训全部归结于郭沫若一身, 从而在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中做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亦有助于达到客观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