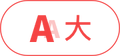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乱宫之变”:洪武宫闱与胡蓝党案关系抉微
胡 丹
摘 要:在马皇后去世后的三年丧期中,洪武朝的后宫发生了多起“乱宫”事件,经过多年的追索,大批妃嫔宫人、勋贵及其子弟被杀。所谓“入乱宫禁”,实际上是明太祖对后宫与外朝交结的夸大认知。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发现,许多乱宫事件的参与者,是胡、蓝党案中的“罪犯”,由此掀开了明初勋贵之家与皇室、宫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研究“乱宫之变”,不仅能揭开明太祖时期宫廷的神秘面纱,也可为深入探究明朝皇室婚姻制度的转变以及洪武朝胡、蓝党案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明太祖;洪武;“乱宫”;胡蓝党案
洪武朝的后期,曾发生多起“乱宫”事件,导致至少一妃、二侯以及众多宫人和勋贵子弟遭到诛杀,实为洪武后期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时民间亦有风传,时人甚至称明太祖“悉诛宫人”。可能是因为明初宫廷史料极为有限,难以深入探研,亦或论者以为,有关明太祖诛杀宫妃的记载皆出野史,未可轻信,因而迄今未见专论。市上所见明太祖传记颇多,但对此几乎无所涉及,这为明初的宫廷史、政治史留下了不应有的留白。
洪武后期连续发生的“乱宫”事件及其引发的追戮——本文称之为“乱宫之变”,并不限于宫闱,它与当时残酷的胡惟庸、蓝玉党案存在紧密的关联,构成洪武晚期时局的一部分。明初“国史”对此隐而不书,如因其子参与“乱宫”而伏诛的江夏侯周德兴,《太祖实录》讳作“帷薄不修”;对另一位因“入乱宫禁”而死的豫章侯胡美,则只字不提。但从洪武朝的榜文、敕编的时政材料以及时人所撰野史中,仍能找到一些零散的材料。对其加以梳理,仍可为讨论“乱宫之变”的真相提供可能。此项研究的价值在于,不仅揭开洪武朝后宫神秘面纱之一角,也为深入考察明朝皇室婚姻制度的转变以及作为明初重大政治事件的“胡蓝党案”提供一个宫闱的新视角。

▲明太祖画像
一、胡美父子“入乱宫禁”与明太祖宫禁防闲之严
后宫发生“乱宫”之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肃清党逆”榜文披露的。
所谓“肃清党逆”,是指洪武十三年(1380)初爆发的丞相胡惟庸案,史称“胡党之狱”。经过长达十年的追论诛杀,洪武二十三年再次掀起高潮: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满门被戮,同时被杀的还有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等一大批勋贵及文武官员。 五月初二日,因党逆基本肃清,明太祖口诏几四千言,命刑部尚书杨靖制作榜文,“备条乱臣情播告天下”。榜文说:
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后,胡党事觉,内有谋逆不仁者济宁侯顾时等十四人,乱宫者豫章侯胡均美。
与其他公侯“谋逆”之罪不同,胡美的罪名是“乱宫”。
胡美原是陈友谅手下的江西行省丞相,至正二十年(1360)归降后,东征南讨,立下汗马之功,洪武三年(1370)封侯。胡美之女为胡顺妃,是洪武三年五月初封的“六妃”之一。
胡美早在6年前的洪武十七年(1384)已坐法而死,却不知所犯何罪,史书对其下场,或不书(如《太祖实录》),或误书(多以为死于蓝玉党案)。 其实榜文已经公开,胡美实死于“乱宫”。今见榜文只是节录,曝其罪行说:
豫章侯胡美,长女入宫,贵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乱宫禁,初被阉人赚入,明知不可,次又复入。且本人未入之先,阉人已将其小婿并二子宫中暗行二年余。洪武十七年事觉,子婿刑死,本人赐以自尽,杀身亡家,姓氏俱没。
“乱宫”又被表述为“入乱宫禁”。由榜文可知,胡美长女在宫为妃,其小婿及二子在宦官引导下,秘密来往宫中两年有余;其后,胡美在明知不可的情况下,为宦官所“赚”(“赚”有骗和诱导之意),也秘行进宫,被记录在案的有两次。
胡美父子在宫中“暗行”,说明他们来往宫中,是瞒着“亲家”皇帝的,这当然不对,有失礼数,可是做爹的进宫看女儿,如何就是“入乱宫禁”?胡氏之女深居后宫,其父兄暗行来往,尚属情有可原,不知胡家“小婿”,也就是胡妃姐妹的丈夫,如何也不顾嫌疑,长久往来?榜文没有公布细节,亦无从猜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胡美父子这么做,大大触犯了皇帝的忌讳!
明太祖以元代宫阃秽乱为戒,将其上升到亡国的高度,如《太祖实录》云:“上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亵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 相关“令典”体现在御制《祖训》中,对宫廷“关防”有着极为严苛甚至是不近人情的要求。以宫人生病为例:
若医人入宫诊治,“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员,当直内使三名、老妇二名,同医人进宫看视。”一个医生进宫瞧病,要求内官监太监、守宫门太监、御药局太监各一人,连同当值宦官三名、宫中老妇(老年宫女)两名,共八人相陪。
若陪同之人不及八人之数,监官、门官、局官各杖一百,当值宦官、老妇各杖八十;若当值太监并各官偷懒,只让老妇引医入内,则将监官、门官、局官问斩,当值太监并医人、老妇皆凌迟处死。
若后宫妃嫔、女孩儿等生病,病情较轻的,就在乾清宫诊脉;只有病情较重,才允许医士白天到病人房中看视,夜间唤医进宫,绝不允许,如违,医士连同请医之人,一并斩首。若是普通宫人生病,轻的,就在宫门看视,重的,出宫送养容堂,由监官、门官、局官、内使人等同医士就彼发药医治。
以上内容见于洪武初制定、洪武十四年(1381)颁布的《祖训录》之“内令”。可能是考虑到医生进宫隐患较大,洪武二十八年(1395)修订的《皇明祖训·内令》将相关内容改为:“凡宫中遇有疾病,不许唤医入内,止是说证取药。”
对宫廷出入,《祖训录》也有严格规定:“凡宫闱当谨内外,后妃不许群臣谒见。群臣妻非夫命无故不许入宫,君亦无召见之理。”
无论妇女,还是太监,凡出入宫城,皆有严格的搜检制度,就连私写文帖于外,写者、接者皆斩。明太祖以严刑峻法来推动宫闱制度的落实,动辄施以凌迟、斩首、剥皮之刑。他还经常提醒在封国的儿子们,不可容令外人出入王宫。在他搜集的诸王“不法”证据中,常能见到男女闲杂人等“引入宫内”“出入宫中”或“入宫住过”“在宫住歇”“在宫宿歇”等内容。就在榜文披露胡美父子“乱宫”的当年二月,明太祖写信给晋王朱,还称其二哥秦王朱樉“终岁玩妇人,为妇人所迷,护卫官军人等,乱宫者无数”。而此前《御制纪非录》条列秦王之恶,特地提到一个王婆子和一个范师婆,她们不仅本人“在宫住歇”“教诱为非”,还常引其子“出入宫内”,甚至“假装内官,在宫宿歇”。
可见,在明太祖的认知里,无论是南京大内,还是诸王王宫,均长期、持续存在“乱宫”行为,“乱宫者无数”。但他对于何为“乱宫”,并无明指,综合来看,大概凡外人私自入宫皆可视作“乱宫”。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他自然不会认为胡美一家出入宫闱是正常的走亲戚。“祖训”明令禁止群臣妻无故入宫,后妃的男性亲属又岂可入内谒见?故斥之为“入乱宫禁”。胡氏父子由宦官引导,暗行宫中两年有余,至洪武十七年事发,胡美赐死,子婿伏诛,榜文称其“杀身亡家,姓氏俱没”,胡顺妃恐难独活。
洪武十七年的“乱宫”案,还有时人的记载作佐证。俞本《纪事录》记:
是年,上疑锦衣卫秦指挥有乱宫事,斩之。妃胡氏谏曰:“深宫严禁,安有此事?”上盛怒,亦杀之。妃父豫章侯胡美,令自缢,妃之兄弟俱斩于玄津桥。悉诛宫人,瘗于聚宝山下。
“乱宫”之事在追索过程中竟达到“悉诛宫人”的程度,说明发现的线索绝不止秦指挥一人。如果胡顺妃仅仅因为进谏就遭杀害,并且累及父兄,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俞本所记应为当时社会传闻,他应该没有看到洪武二十三年的榜文,否则不会不知胡美父子有“乱宫”之事。晚明人张大同在此条下注云:“(俞)本疑秦指挥乱宫,此以讹传讹之妄也。”《纪事录》中提到的秦指挥“乱宫”以及“悉诛宫人”,确实是榜文没有的,但未必一定是“以讹传讹”。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与马皇后
二、胡蓝党案中的勋贵子弟“乱宫”
洪武二十三年,党案再兴,多位公侯以胡党之罪诛死,此后时局进入一个相对的安定期。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标突然薨逝,这是洪武十五年(1382)马皇后去世后又一次宫廷大变。八月十一日,朱标被谥为懿文太子,入葬于其父陵寝孝陵的东侧(今孝东陵)。就在朱标发丧祔葬的前一天,朝廷发生了一件不太引起后人注意的事件: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伏诛,命收其公田”。
江夏侯周德兴,不仅与太祖同里,还是少年时的朋友。 在当时还存活的开国元勋中,以周德兴“年最高,岁时入朝,赐予不绝”。这样一位“从小玩到大”的老臣,依然没能逃脱被诛的命运。
《太祖实录》将周德兴之死归为“帷薄不修”,语出自贾谊《新书·阶级》:“坐污秽男女无别来者,不谓污秽,曰帷薄不修”,是古代对“贵大臣”德行污浊的一种讳言。可是,如果周德兴仅仅只是私德问题,怎会遭到诛杀的严惩呢?《明史》揭开了真相:“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周德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正如钱谦益所言,“国史所记帷薄不修,盖亦史官之微词”。其实,只要仔细梳理当时史料就会发现,周德兴父子之死,是洪武十七年以来,一系列“乱宫之变”的一个小高潮。
朱元璋敕编的一种时事文本《逆臣录》,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诛杀凉国公蓝玉后,汇集“蓝党”近千人的口供而成,其中“右都督王诚”下记道:
洪武十六年间,有男王庸,同朱都督男、江夏侯男周骥,纠合入宫为非。是(王)诚彼时明知此事,不行禁戒,故纵犯法。
说的是洪武十六年(1383)时,蓝党罪犯、右都督王诚之子王庸,伙同朱都督和江夏侯的公子入宫为非,王诚明知不可,却不加制止,属故意纵子为非,其中提到上一年八月因“帷薄不修”伏诛的江夏侯男周骥。都督王诚的罪名之一,跟周德兴一样,也是其子“乱宫”,不行禁戒,最终“并坐诛死”。
又据《逆臣录》,金吾前卫带俸指挥朱铭供称:洪武十六年,他和府军左卫带俸指挥徐质、羽林右卫指挥陈义,时常与崔姓内官“交相猜拳戏谑,饮酒情熟”,在某月某日(失记月日),央求崔内官引领入宫,在西华门里板房潜坐,至起更时分,引到女子三名,与之各行奸宿,至天明送出门来。此后“节次入内为非,一向倖不败露”,只到追究蓝党时,才事发落网。
朱铭的供词提供了一些“入宫为非”的细节,即由相熟的宦官引入禁城,在西华门里的板房,与三名女子奸宿,直到天明才出来。他们不止干了这一回,此后多次入宫为非,一直不曾暴露。值得一提的是,板房是太祖本人经常临幸的地方,在官史记载中,他常在板房读书或召见侍臣,可见得是近御的非常之所。徐质、陈义“各招与朱铭相同”,大概他们二人是由朱铭供出来的。
《逆臣录》所收供词众多,有许多不可思议、不合常理之处,让人怀疑出自屈打成招,是不太可信的自诬之词。朱铭的供述就是这样,他说他与徐、陈三人,由相好的内官引入西华门,与女子奸宿,可是那起更时分引来的女子是谁?他们几个如此色胆包天,竟敢入宫奸宿宫人?而且还是“节次入内为非”!如果此事可信,大明的后宫,岂不成了放浪武官的风月场?
根据《逆臣录》所收供词,“江夏侯男周骥”与王庸、朱都督男(未知是否就是朱铭)等纠合,入宫为非,始于洪武十六年。而江夏侯父子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伏诛,已在十年之后。莫非这几个冒着族诛的风险,行此大逆不道之事,长达十年之久?而周骥事发,父子受诛,竟然没有影响到王、朱等人,后者在洪武二十六年初追究蓝党时,才“今因事发”,这可能吗?周骥被获时,难道不会供出他的同伙?
以上乱宫之人,凡身份明确者,皆为京卫指挥,卫分包括金吾前卫、府军左卫、羽林右卫和锦衣卫。朱铭、徐质在《逆臣录》中明确记为“带俸”官,王庸、朱铭是都督之子(王庸在案发时已升任都督),豫章侯的子婿以及江夏侯男,很可能也是以勋贵子弟的身份在京卫带俸或任实职。以上信息隐约透露出:洪武十六、十七年(1383—1384)“乱宫”案的主角,皆为侯、都督等高级将领的子弟;他们的乱宫行为,全部暴露于追究逆党的残酷斗争中。这或许说明,所谓“入乱宫廷”,其实是大兴胡、蓝党案时所设的一个陷人的筐儿!所以极尽追索攀引之能事,乃至十年前的“乱宫”旧事,在蓝玉之案中集中“暴露”。
将上述乱宫行为加以梳理排列,可使其脉络更加清晰:
洪武十五年,胡顺妃父豫章侯胡美及其子、婿先后入乱宫禁,有两年之久,十七年事发,妃死,胡美父子诛。(见刑部榜文)
洪武十七年,上疑锦衣卫秦指挥有乱宫事(未知秦指挥是否即是胡美的小婿),诛胡顺妃及其父兄弟,并悉诛宫人。(见《纪事录》)
洪武十六年,都督王诚子王庸、都督朱某子、江夏侯子周骥,多次纠合,入宫为非。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父子事发伏诛,二十六年王庸父子事发伏诛。(见《逆臣录》)
洪武十六年,金吾前卫带俸指挥朱铭、府军左卫带俸指挥徐质、羽林右卫指挥陈义,与崔姓内官勾结,节次入宫为非。二十六年事发伏诛。(见《逆臣录》)
可见,乱宫行为主要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到十七年的两年间,可分为“胡顺妃及妃家父子”与“江夏侯子、都督王诚子、都督朱某子”“指挥朱铭、徐质、陈义”三条线,涉及到两家开国侯(江夏侯、豫章侯)与若干功臣子弟(多在京卫担任指挥等高级武职)。
两案所涉宫人,包括妃子(胡顺妃)、宦官(赚入胡美父子的阉宦、崔内官)和宫女(三名夜至板房宣淫的女子)。明太祖在暴怒之下,严厉追查,在内廷大开杀戒,杀死被攀指的妃嫔宫人,是完全可能的。俞本所记“悉诛宫人”,或有所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草木子余录》记洪武十七年李文忠死后,“戮内监将千人,又并杀后宫妃嫔近千人”。该书作者叶子奇,与俞本同为洪武中人,他们的记载,可彼此参看,反映了当时民间盛传的某种骇人的舆论。
在洪武二十三年满门被诛的韩国公李善长,他的罪状也涉宫闱。
明末清初史家万斯同(字季埜)曾问吴乔,明初诗人高启诗云“小犬隔花空吠影”,意何所指?吴乔答:“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室,李善长子弟有窥觇者,故诗云然。李(善长)、高(启)之得祸,皆以此也。” 明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御制大诰》中亲口承认,他因恼怒陈友谅多次入犯,“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吴乔言之凿凿,称掳来的陈友谅姬妾藏于别室,李善长子弟窥伺,高启写诗讥讽,后二人俱因此得祸。吴乔之说虽不可信,但已微露勋贵子弟“窥觇”宫闱的隐情。吴中野史也有类似说法,钱谦益初以为无稽,并不相信,但后来在翰林院修史时,“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则知季迪(高启字)此诗盖有为而作”。
洪武二十三年《昭示奸党录》的性质与公开蓝党罪行的《逆臣录》相似,收录了“胡党”案犯李善长及一干功臣的罪状与供词。钱谦益没有指出“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的具体内容,但他将其与因“乱宫”被诛的胡美父子连起来说,辄知爰书所涉,定是见不得光的宫闱秘事。
钱谦益是最早发现“乱宫之变”的历史痕迹的学者,但他可能有所忌讳,未能深辨,如其所言:“余于诸招,自临川侯(胡美)外,如李善长之二子,及费聚之子越,杨璟之子通、达,德兴之子骥,皆削而不载。后之取征者,考《奸党》《逆臣》二录全招,则知之矣。”语意含蓄,但隐约指出了线索。惜《昭示奸党录》一书今已不存,然如上文所考,临川侯胡美子婿、李善长二子、周德兴子既皆涉“乱宫”之事,则钱谦益“削而不载”的招词中,还有平凉侯费聚子费越、营阳侯杨璟子杨通、杨达,共五位开国公侯的子弟,即众多“小侯”,亦涉“乱宫”之事。易言之,在五位公侯的致死罪名中,都包含其子弟“入乱宫禁”的罪状。
从《逆臣录》所收招词来看,那些因与蓝党而诛的乱宫者,往往还有其他结交胡、蓝的罪行。如会宁侯子张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六月某日,其父张温在家饮酒,对他兄弟密说,“我当初见胡家有权时,同李太师、延安侯、江夏侯男周骥都去交结,不想事谋未成,险些儿被他累了”。可见,周德兴父子也因告发牵入胡案,他们在蓝党之案爆发前夕被杀,主要罪状是周骥乱宫,自属附会之罪,所以与周骥同乱宫者未遭追究,而次年蓝案大兴,这些人就在彼此的攀染中通通落网了。于此可知,“乱宫之变”与当时残酷的党案,是紧密纠缠、关系复杂的。
▲影视剧中的明代后宫
三、“乱宫之变”与李淑妃、郭宁妃摄六宫之政
上述“乱宫”事件发生的洪武十五年到十七年,正好在马皇后去世后的三年丧期之内,这个背景必须注意。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大明后宫没了女主人。《太祖实录》的《马皇后传》写道:
(后崩)上恸哭,终身不复立后。上尝罢朝,内臣、女史更进奏事不已,上凄然不怿曰:“皇后在,吾岂有此烦聒哉!”后在时,内政一不以烦上,上从容甚适,故不胜哀悼焉。
明太祖思念马皇后,决定终身不再立后,然而,在他的观念里,后宫无主必为乱阶,这从他对诸王的教训可知: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朱樉为宫人“毒害”,明太祖在分析原因时,反复提到秦王“于宫不立正妃,宫且无主,小人杂进”,“秦(府)有事,皆是宫无主,主宫者无昼夜杂处。……(今中毒而)亡由正宫被苦,因宫禁不严,饮食无人关防计较”。 四月初五日这天,晋王收到两封太祖亲笔书信,其中三次提到秦王“正妃”“正宫”,认为秦王妃被“打入冷宫”,致使后宫无主,宫禁不严,小人入宫杂处,是造成秦王遇害的根本原因。 明太祖的这种心理,无疑会体现在他对大内“乱宫”行为的认知上。难道他不会认为,洪武十五年以来,后宫连续发生“乱宫”之事,不是因为后宫无主?
故此,他虽然决定“终身不复立后”,但还是需要选择一位“贤淑之女”,帮助自己奉宗庙、理内治。洪武十七年十月,恰满马皇后三年之期(古代服丧三年,实际上只有27个月),他马上册立了一位李氏为淑妃。
李淑妃是前广武卫指挥佥事李傑之女,册文说:
妃嫔之立,所以助皇后,奉宗庙、理内治也,非淑德贤行,曷膺兹选。朕自后崩之后,欲得贤淑之女,助朕奉祀宗庙,乃卜诸功臣之家,惟尔李氏最贞,特册尔为淑妃,助朕以奉宗庙之祀。尔惟敬哉!
李傑生前不过是四品武官,早在17年前的洪武元年(1368)就战死了,李家似乎很难称得上“功臣之家”。李淑妃的妃号也有问题,《太祖实录》记立李氏为淑妃,但洪武晚期翰林学士刘三吾为妃家追封先代撰写的墓碑,却记道:“(李傑)女李氏,今为皇淑妃”;李傑神道碑也说:“女一人,今即皇淑妃。”碑文记载可信,淑妃之号上应有一“皇”字。想来《太祖实录》并无隐晦的必要,可能李氏初封为淑妃,随因宠进封皇淑妃。
册文说:“朕自后崩之后,欲得贤淑之女,助朕奉祀宗庙”云云,短短74个字中,“助朕奉祀”这样的表述就出现两次。显然,李淑妃承担了辅佐皇帝“奉宗庙、理内治”的职责。洪武后期,“皇妃”是比贵妃更高的妃号,“册而兼皇,以君视之”,等于是不居皇后之名的摄皇后。拥有这个封号的,只有两人,一位是李淑妃,另一位是郭宁妃。《明史·后妃传》据此才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孝慈皇后服除,册封淑妃,摄六宫事。”
据册文讲,马皇后去世后,为选一位贤淑之女,“乃卜诸功臣之家”。说明李淑妃是在马皇后“崩”后(甚至可能是在丧期正式结束后)才选入的,入宫时间并不长。然而,一个宫廷新人,马上被册立为妃,并且取得类似于皇后的地位,这就很有点不同寻常了。
有学者将洪武十七年的“乱宫之变”与同年李淑妃册立“摄六宫事”结合起来,推测:明太祖在宫变中,尽屠诸妃,包括洪武三年初封六妃中的五位:胡充妃、郭惠妃、达定妃、胡顺妃,以及在皇后丧期“摄六宫事,称皇妃”的郭宁妃(六妃中居首的孙贵妃十年前已死)。其推论逻辑是:只有在“悉诛宫人”的条件下,才会让李淑妃这样一位资历及年龄均浅的新人,甫入宫即主持六宫之政。
如果从研究的科学性上来说,有确凿的史料证明死于洪武十七年宫变的妃嫔,只有胡顺妃一人(也是根据榜文“杀身亡家,姓氏俱没”的说法推定的)。在后世野史中,胡充妃、达定妃皆为明太祖残杀,但未可定为信史,且野史所记“死法”,也与洪武十七年宫变无关,于此不论。然而,郭宁妃却有较大可能死于该年,这一点耐人寻味。
在洪武后期的宫廷中,郭宁妃不仅资格最老(早在濠州时期,妃父郭山甫即预言太祖“贵不可言”,并“遣妃侍太祖”),地位也可说最高(在李淑妃之前摄宫政,且封皇宁妃),她还是鲁王朱檀之母,她的两个哥哥先后封侯,其中武定侯郭英还是洪武中硕果仅存的几位开国功臣之一。郭英极得太祖宠信,两家亲上加亲,郭英有二女嫁给皇子,子郭镇尚永嘉公主,最长的孙女许给了燕王世子朱高炽(未来的仁宗)。郭英本人经历了靖难之役,一直活到永乐元年(1403)。可见在太祖诸妃中,郭宁妃的外家根基最厚。
无论是明朝万历中作为官修“国史”成果的《皇明后纪妃嫔传》,还是清人修的《明史·后妃传》《胜朝彤史拾遗记》,均记郭宁妃在马皇后死后“摄”宫政。但马皇后丧满后,不知什么原因,太祖没让这位事实上的后宫之主转正做皇后,甚至没让她继续主六宫之政,而是另立新人李氏为淑妃,“奉宗庙之祀”。这令人对郭宁妃的结局起疑,而史料中又确实有郭宁妃未得善终的可疑线索。
郭宁妃的二哥巩昌侯郭兴,正好死在“乱宫之变”发生的洪武十七年。郭兴是当年十二月下葬的,他应该死在几个月前,与胡美被诛的时间相当接近。郭兴神道碑是郭兴去世三年后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奉敕撰写的,对其履历的记载极为简略,仅称:“进封巩昌侯。方倚之永镇西陲,而溘先朝露,薨于家矣。” 郭兴封侯在洪武三年,碑文对其后14年的事迹,竟不着一字,也没提到郭兴为何在54岁的盛年突然薨逝。郭氏一门最大的荣耀,自然是郭家兄弟的妹妹为太祖之妃,且是主持宫政的皇宁妃,然而这篇敕撰的神道碑,在介绍郭氏至亲时,竟然没有提到当朝的郭宁妃!
宣德中,大学士杨荣为去世二十多年的武定侯郭英(死于永乐元年)撰写神道碑,提到一件皇恩浩荡之事:洪武四年(1371),郭英升骠骑将军、河南都指挥使,“将赴镇,皇宁妃,公之女弟也,上遣至公第饯之”。证明郭宁妃确曾进封皇宁妃。碑文说郭英出镇河南前,太祖特地安排他的妹妹入府,为之饯行,郭宁妃乃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郭英神道碑里。然碑文所记,亦仅此而已,碑末屡述郭英至亲,如郭英之女为辽王妃、郢王妃,孙女为仁宗贵妃,无不写到,唯独不提郭英之妹为太祖宁妃。
二郭兄弟的神道碑文如此一致,不能不让人怀疑,郭宁妃可能非善终,以至于郭兴墓碑不敢提及她;杨荣为郭英撰写墓碑时,时过境迁,虽然在一件颂圣往事中提到郭宁妃,却也在介绍家属时刻意回避了她。由此疑窦进而思之,洪武十七年发生“乱宫之变”时,正由郭宁妃主持后宫,她难道不会为此承担责任吗?朱元璋在“悉诛宫人”时,将为“乱宫”承担“领导责任”的郭宁妃杀死,或迫令其自杀,都是有可能的。郭兴在洪武十七年发生宫变时突然去世,会不会是因为受了郭宁妃的牵连,被迫选择自尽?故神道碑讳其死,且语多遮饰。洪武二十三年,当再次追论胡党时,郭兴虽死,亦遭身后夺爵。
前引曹国公李文忠亦死于洪武十七年。一年之中,死一公二侯,胡美为赐令自尽,而郭兴(54岁)、李文忠(46岁)皆为含有隐情的骤死,难道纯属巧合?时人记太祖因疑李文忠为小淮安侯华中毒死,贬中爵,放其家属,且诛医士:俞本《纪事录》记“应天府医士全家被诛”;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记“族诛城内外大小医家及保保(笔者按:文忠小字保保)婢妾六十余人,并戮内监将千人,又并杀后宫妃嫔近千人”。似文忠之死引发了牵连京城医家的大案,进而染及后宫,大批内监与妃嫔被诛,这与《纪事录》所记洪武十七年“乱宫”案中“悉诛宫人”亦能彼此印证。
结 语
综上所述,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后,因后宫无主,又发生了豫章侯胡美父子“暗行宫中”之事(民间传言还有锦衣卫秦指挥乱宫),明太祖遂疑外臣“入乱宫禁”,乃于洪武十七年大肆诛戮,胡顺妃作为直接当事人被杀,郭宁妃则以失职死。经过此事,明太祖常疑京卫武臣与宦官、宫人勾结,私自入内为非,当洪武二十三年再次追究胡党、洪武二十六年追查蓝党时,众多高级将领及其在京卫任职或带俸的子弟(诸小侯、勋卫),纷纷被揪出所谓的“乱宫”之罪。考《逆臣录》所收都督王诚招词,云:“因洪武十一年间,与同申国公(笔者按:邓愈子邓镇)结交胡丞相。又有男王庸,纠合江夏侯男周骥等入宫为非。虽是上位恩宥免问,为见在后各官节次事发被诛,心中惧怕不安。今被凉国公纠合谋逆,以此听从。” 这样的供词明显不可信,设若王庸、周骥“入宫为非”早已为太祖获知,他岂肯“恩宥免问”?不过是在追究王诚父子等从蓝玉“逆谋”时,硬扒出来的罪名罢了!
明初帝室多与功臣结姻(如涉“乱宫”案的胡美、李善长、郭兴、蓝玉等,皆以功臣兼戚臣),后者与宫中颇有联系,甚至可能通过宫人、宦官牵线,私下来往,虽大触帝忌,但未必真有“乱宫”的行为。然而在洪武后期残酷打击勋臣武将的政治斗争中,这种内外关系极易成为“入乱宫禁”之罪,遭杀身亡家之祸。自此之后,明太祖也不再与功臣勋贵结亲(李淑妃只是名义上来自“功臣之家”),洪武后期一系列以血腥收场的“乱宫”大案,促发了帝室婚姻政策的转变。
由于史料缺乏,洪武中的“乱宫之变”依旧迷雾重重,某些结论只能止步于推论。然而综合考察来源不同的诸多记载——既有官方刊印的时事材料,也有同时代人所记野史,以及后人围绕此事的谈论——已大体能窥见真相的朦胧面目。将这幕发生在宫廷的血腥图景与整个洪武后期的政治屠戮放在一起考察,可以为深入研究胡、蓝之狱,补充一个过去缺失的宫闱视角。
作者简介
胡丹,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史、新闻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