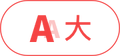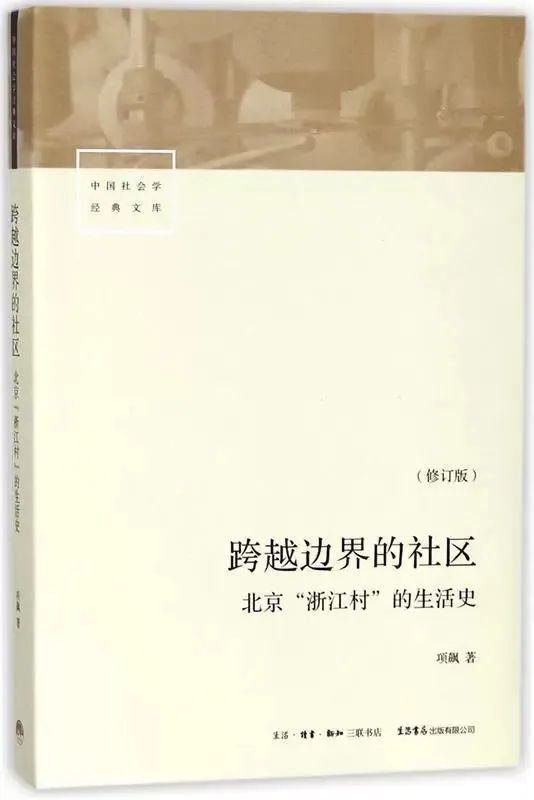01.
前些日子,与一位老友约着吃个饭。地方是他选的,一家江西菜小馆,名字叫禧芗莲,在朝阳门的新店开了不久,在江西老乡圈子里暗暗流传。老板是江西抚州人,做一些风土风味,踏踏实实的一家好吃的小馆子,我们两位,在餐厅里点了不少菜,都是江西土菜,诸如皮蛋肉饼汤、烧鱼籽鱼泡、爆炒土鸡、瓦罐煨汤……还兴起加了一瓶四特酒。
老友说,想找一家有意思的餐厅还真不太容易。许多大店名店都太熟悉了,厨师经理都认识,难免应酬;北京的街边小店往往味道平庸,细节不够,出彩的不多。既要有一些味道,又要有一些讲究,还要有一点陌生,他思来想去,选择了一家新开不久的江西菜。

江西菜,在北京不算主流,与川湘菜相比。也跟餐厅服务的大姐聊天,他们最早的一家店是开在丰台,丽泽桥附近。如今丽泽桥周边已经成为拔地而起的商务区,往回倒20年,附近还是批发市场,西南郊冷库以及城中村。
那时候,我也会去丰台,路过铁道桥,地面扬尘,干涸的水渠,坑洼的路面,感觉是出了城。那时候去丰台往往是采访,顺便吃饭。在20年前的丰台城中村中,往往就可以吃到地道且便宜的江西菜,因为附近蔬菜批发市场里聚集着一批做批发生意的江西人,有族群聚集的地方,就会有当地风味。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于是有了这篇文章的想法:关于地方风味的进京路径,官方的,民间的,挂牌的,隐秘的,宏大叙事的,暴土扬尘的……味道的进京之路与人才的进京之路似乎可以遥遥对应:一种是分配,留京指标,人才引进,积分落户;一种是北漂,外来务工,劳动力输出。
它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隐喻,更是一种坚硬的事实。二元结构的城市,政治喻体的首都,美食的荒漠与天堂,都在人间。
02.
上世纪50年代,一批全国各地的餐饮门店陆续进京。当时已经完成了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各地知名餐厅都完成了国有化改造。周恩来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业”的号召,一批服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名店陆陆续续落地北京。
川菜有峨嵋酒家、力力餐厅,四川饭店;上海菜有致美斋;湖南菜有马凯餐厅,曲园酒楼……这些餐厅大多数都还在,后来归到各个区的饮食服务公司,又在改革开放之后历经各种改制,到现在成为各种老字号以及国有控股企业。
许多北京人把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当成标准
这一时期从各地搬移到北京(或者抽调各地团队在京组建)的地方风味,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除了服务大众,也有很强的政府接待宴请的任务。我也认识不少曾经在这些餐厅内工作多年的老厨师,许多人都有过接待重要宾客的经历。
“驻京办饮食风潮”的兴起,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驻京办,是现在的称谓,其实历史悠久,其前身是各地会馆。新中国成之后,各地政府在北京设计办事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职能是向中央政府争取物资支持。1966年底至1967年驻京办事处被撤销。1978年驻京办事处相继恢复设立,主要职能是联系国家有关部委,做好与中央各部门的业务联系工作,负责大型项目的落实,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派出地政府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其所担负的职责日益增多,内部分工也日趋完善,进而形成业务联络、信息处理、接待服务等职能。
也就是在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各地驻京办的兴盛,形成了北京独有的一种饮食路径:驻京办饮食。
驻京办有大有小,从省级到市级,在住宿功能之外,也会有一家餐厅,提供本地风味。一边对内接待,一边对外营业。一方面,餐厅的厨师与服务人员都来自当地,不少人都还有体制内身份;一方面,只需要做好家乡口味,做好接待,并没有很强的经营考核压力,呈现出一种五花八门的原生态的质感。
在我20多年前刚入行做美食记者的时候,就隔三差五做关于“吃遍驻京办”的专题内容,当时最火的驻京办是建国门的四川驻京办,简称“川办”,直到前些天,美国财长耶伦来北京,还选择在川办吃一顿中餐。
当时我写的一句吃办事处的顺口溜也流传至今:“省不如市,市不如县,正不如偏”,越是小地方的驻京办越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在广西驻京办要吃一碗螺蛳粉,在兰州驻京办吃雀舌面,云南驻京办腾云宾馆吃汽锅鸡,但是要想吃生皮,就要去大理驻京办的蝴蝶泉;安徽驻京办固然不错,要想吃独特的要去居民楼的池州驻京办;当时北锣鼓巷里有一个凉山州的驻京办,叫金色凉山,可以吃到大块的坨坨肉;而在西城区的一家胡同里,有攀枝花驻京办,名字叫大笮风。人们经常争辩:“乌办”(乌鲁木齐驻京办)与“巴办”(巴州驻京办)哪个更好;要吃江苏菜要去常州办或者扬州办,想吃湘菜则去长沙办或者永州办……
兰州驻京办的雀舌面 图by princess1004
2000年-2013年,这十几年是各地驻京办的地方口味在这座城市红红火火的岁月。后来各地驻京办慢慢撤销,餐厅也更多成为社会化酒楼。
在十几年前,这些驻京办成为北京食客窥探不同地域风味的重要窗口,古早食客通过在驻京办餐厅消费完成了中国味道的味觉拼图游戏,而不同省份的异乡人更是在这些故乡滋味中寻找到了某一些情感寄托。在那些年,商业地产ShoppingMall 尚未崛起,如今风风火火的地方菜系的诸侯还在酝酿时期,北京街头的餐饮还是酒楼模式为主,这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驻京办文化,成为不同地域的风味进京的通行证。
这种挂牌的乡愁,如此明晃晃,进京之路笔直清晰,口味骄傲且堂皇,这是地方口味的A面。
03.
当然也有B面。
B面在郊区的城中村,以及批发市场中。这是地方风味进京的隐秘之路,它们沉默,毫不声张,构成了我们身边的异乡。
就如同上面提到的江西菜往往发迹于西南三四环的丰台,温州菜往往发迹于大红门,福建菜(特别是莆田菜)往往发迹于十里河。
像北京北京这种大城市之中,打工者往往抱团取暖,形成行业同盟,或者同乡会的互助组织。在背井离乡的环境中,方言是一种通行证。越是区别于北方官话佶屈聱牙的小众方言区域,越是容易产生抱团效应,从而形成聚集村落,并且衍生出不为人知的小众地方饮食。相对应的,北京周边省份(山河四省)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是散沙状态,很难形成聚集效应。
当年的浙江村就是一种典型案例。知名学者项飙还以此为研究课题,出版过一部社会学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
这本书的自序中,项飙写道:“北京城南浙江村近20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他在1992-1998年的六年的时间里,深入浙江村记录了这里的社会变迁,乃至衣食住行,哪怕现在浙江村已经成为过往,在这本书里还恍惚如昨。
在这本书中写道:“1988年前后,浙江村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服务体系:自己的菜市场,自己的饭馆,自己的幼儿园、自己的诊所、自己的理发店……在这各地移民聚居区中,是个普遍现象。”
菜市场,餐厅延续到现在,在大红门还有鑫江南生活超市,这里面可以买到温州的年糕,米糕,各种咸菜,海鲜,米粉,乃至温州本地的调味品;也有一些温州风格的餐厅,延续到如今。比如非常红火的迎春面馆,当年还是在批发市场里面的一家温州海鲜面,现在依然有许多年轻人慕名而至。
大红门的温州海鲜面和水产市场
在不远处的沙子口区域,是传统的文具用品批发市场,是潮汕人聚集的区域。这里也隐藏着一些独特的潮汕滋味,比如盛中钰广味小馆,在一个破败的礼品中心商城的半地下,需要穿过破败的散台区域进入包房,可以吃到一些质朴的潮汕菜。有虾枣,生腌,普宁豆酱烧杂鱼,也有螃蟹血蚶种种卤水。当潮州菜以一种昂贵精致的高级料理出现在北京其他热门商圈的时候,在南城,还有一些市井的潮州滋味。
除了这家餐厅,也有一条街区,专门出售种种潮汕风味小吃,包括卤水咸菜种种调味料金桔油或者鱼露。这些小吃店毫不显眼,具体在西罗园北路,距离地铁永定门站不远,这些小店是客居北京潮汕人的乡愁。
如果你去过宋庄,会发现有许多口味地道的湖南菜,我经常去一家叫香菜湘的小店,招牌菜是金钱蛋烧拆骨肉,其中的金钱蛋堪称宋庄的“庄蛋”。在2024年宋庄湘菜好评榜的前三位分别是:小湘旺、园味湘食、常德派艺术餐厅。宋庄尽管居住着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家,遍布着各种艺术工作室和画廊,但是批发画材,艺考培训、开彩印店的全是湖南人。湘菜才是这里的霸蛮味道的底层基础。
郊区,外来人口,城中村,批发市场,扬尘,脏乱差,中国特色的牌匾招牌,沉默的面孔,飞驰而过的电动车……这些都是北京的另外一侧。2017年,经历过一场运动之后,这些聚集群落逐渐零散,原子化生存。当年小武基大柳树区域流行的安徽皖北风格的餐厅我已经找不到了,前几天开车经过皮村,那种野蛮生长的模样依稀残存着世纪初的北京图景。
这些口味的聚集路径发生在每一个大城市。深圳的城中村中,东北饺子与烧烤与湖南小炒潮汕夜糜交相呼应。遥远的东京池袋,聚集着风味特色迥异的中餐,开店的人是中国人,吃饭的人也是中国人,甚至连菜单也都是中文。它们慰藉着漂泊者的胃口。
无论是驻京办还是城中村,它们共同塑造了一座城市的味觉生态。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丰富着一座城市的味觉体验。它们是两条路径,貌似不交叉,实则彼此纠缠,成为这座城市发展历程中时代的口感。
撰文 | 小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