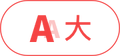骑马武士俑 北齐 祁县白圭镇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彩绘釉陶戴羃公式女骑马俑 唐代 张士贵墓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三角形银车轮饰 战国 甘肃省博物馆藏
波杰托 骑马的轻骑兵 青铜 私人收藏
◎王建南
展览:马——从地中海到江南的千年权力象征
展期:2025.1.17-5.18
地点:苏州吴文化博物馆
今天,当我们回顾马的历史,实际上是在回望自古以来马与人的关系史。2025年开年,一场名为“马——从地中海到江南的千年权力象征”的展览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特展集结了来自中意两国十余家博物馆所藏与马相关的百余件文物,沿着由西至东的地理空间线路,将远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与秦汉时期的江南贯穿在了一起,并为之限定了一个清晰的主题词——“权力”。展览通过中西对比,探索马作为权力的象征如何与人类文明社会展开长达千年的互动。
战争中的马
马本是一种代表着速度和力量的动物。五千多年前的亚欧大陆上,人类出于实用目的开始驯化马匹,其后对马的大规模饲养及军事化训练,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影响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
人类驯服马匹后最初主要是用以驾车。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人类骑乘马逐渐多起来,骑兵因此逐渐得到发展。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是较早发展骑兵的。亚述之后,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军队都进一步发展了骑兵。公元1世纪时毁于火山喷发的罗马庞贝古城中留下了一幅彩石镶嵌的大型壁画,描绘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大流士三世的决战情景,其中便有骑兵场面。
骑兵一直是战场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第一位完全理解其威力的西方将领是北非古国迦太基的军事家汉尼拔。公元前216年,他在坎尼会战中指挥骑兵实施钳形战术,包抄强大的罗马步兵,取得了胜利。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骑兵部队一直在战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到机动车辆的出现,骑兵的作用才逐渐衰弱。
展览中几幅油画作品描绘了骑马的士兵,他们或是在等待战斗,或是在战斗中。格拉内里的两幅画作描述了源于匈牙利的轻骑兵及源于斯拉夫的斯拉沃尼亚兵团。青铜雕塑则展现了士兵们在战斗中的瞬间:法国围攻都灵时,欧根亲王观察形势时陷入沉思;波杰托塑造的青铜轻骑兵在马背上转身,观察后方敌人;克雷斯皮创作的骑兵则向前探出身子,以专业的姿态执行侦察任务。
来自都灵皇家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的黑漆高足盘上绘有一匹踢蹬前蹄的马,器物的材质为公元前4世纪淡棕色细泥陶。腾跃的马象征着受控的力量与受限制的自由,暗示了古希腊文化中对保持力量平衡的追求。这是一匹受到权力控制的马,象征着拥有它的主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与威望。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比单匹战马更为重要的是马拉的战车,它是军事和政治权力的重要象征。公元1世纪的白色大理石浮雕《行进中的战车》虽然残破得只剩下车体和马,但牵马的缰绳表明主人对马匹的掌控力。这通常与神祇或取胜的英雄相关。
中国在商代晚期已有武装骑士出现,河南安阳殷墟中曾发现武装骑士及其乘马的遗骸。此后战车兴起,直至战国时期,骑兵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战国七雄”日益重视骑兵,从而发展成为与战车并列的快速机动兵种,秦楚等大国形成了“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兵力结构。
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了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东汉铜车马仪仗,这是一组完整的铜雕塑,展现了当时汉代高官们日常出行巡视的状况。来自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东汉《车马出行画像石》前有残存的轺(音同遥)车尾部,后有两辆轺车紧随。人物刻画逼真,马的姿态生动。车马出行图是汉代装饰艺术中常见的题材。
说到骑兵,不得不提唐太宗李世民与他心爱的六匹坐骑,它们为李唐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纪念它们的功绩,唐太宗特命负责其陵墓修建工程的工部尚书阎立德设计建造了六骏的浮雕像于通向陵墓的道上。浮雕的稿本应为阎立德之弟阎立本所绘。
本展以六骏的拓片为核心,单独布置了一个展陈空间,彰显出唐代人对马的重视。观众站在其中,环顾四周的六骏拓片,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唐人雄强刚劲的审美观与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生活中的马
除了现身战场,经过人类驯化的马匹还是古代社会人们从事生产不可或缺的帮手、生活中的重要交通工具和人际交往中的身份标志。同时,在不同地域间的商贸往来中,马除了是任劳任怨的运输工具外,还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动物,在人类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中产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自公元5世纪起,法国北部、佛兰德斯地区和德国大型集市兴起,这些集市每年都会举办活动,欧洲的国际贸易网络由此得到巩固,马在这个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都灵市立现当代艺术馆收藏的布面油画《萨卢佐集市》创作于1880年,作品描绘了萨卢佐的牲畜集市。主角是一匹西班牙种马,来自安达卢西亚地区,马的体型描绘精准。右侧一匹尚未完全发育的幼年棕毛马,在喧嚣中显露出些许紧张。
另一幅《蒙卡列里集会》展现了一个生动的乡村集市场景,聚焦于动物集市的繁忙氛围,其中马匹等动物是农民、商人和社区之间互动的核心。画中对马匹的描绘,既突显其在乡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又寓意力量、繁荣与实用性的结合。
而该馆收藏的19世纪油画《驿马》则描绘了两匹健壮的马立在墙边休息的场景,暗示传统运输方式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没落。画作散发着一种怀旧的气氛。
与东方的王侯将相习惯在陵墓前的墓道两边塑立马匹与人像不同,西方的国王与贵族喜欢在市中心广场上安置自己的骑马雕像,以起到纪念碑的效果。
意大利威尼斯广场上的青铜战车雕像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战利品。在中世纪的宗教图像中,骑在驴背上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的情景被当作凯旋的象征。此后,当新任的主教抵达教区时,他的形象往往被描绘成骑马的形象。在教堂或市政厅的墙上,圣骑士的形象也十分常见。他们身着盔甲和军事饰品,成为城市的保护者。
欧洲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骑马肖像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与王权和领主的统治密切相关,请画师绘制骑马肖像在贵族圈里广为流行,这一做法延续至现代。
画马与塑马
在西方骑士精神流行于中世纪欧洲上层社会之前,中国早已进入了秦汉大一统的国家时期,然而此时来自于北方“马上民族”的威胁已成为需要举全国之力来解决的大问题。面对强悍的对手,秦汉政权大力发展骑兵,于边郡广设官方养马场,并通过以马代役等形式鼓励民众养马。
汉武帝时期更是积极引进乌孙、大宛良马来改良马种,并栽培苜蓿改良草场,使得汉马的品质与数量大幅提升,为汉政府对匈奴的守势转为攻势奠定了基础。伴随着骑兵地位日升,商周时期最为看重的马车逐渐由军用转向日常生活和仪仗之用。
山西博物院的北齐《骑马武士俑》上可见秦汉骑兵装束的延续。骑于马上的武士昂首挺胸,注视前方。他身背箭囊,上着甲胄,下穿马袴(音同裤),足蹬马靴,马同样穿戴着护甲。这是一个重装甲骑兵的形象。
隋唐时期出土的墓葬中可见大量的骑马俑,又成为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延续。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彩绘男骑马俑》身着浅蓝色右衽圆领紧袖长袍。所骑之马体态雄健,臀部和腿部塑造的肌肉和骨骼比例协调,显得浑圆而不臃肿。背部塑造了鞍鞯,马尾挽缚打结,尾尖翘起。
这类文物中最少见的是女子骑马俑。同样来自昭陵博物馆的唐代《彩绘釉陶戴羃公式(音同密离)女骑马俑》真实还原了当时女子的出行场面。该女俑头戴羃公式,身穿短襦长裙,脚踩马镫乘于马上,神情悠然。马低头张口,剪鬃缚尾,墨描络头,前有攀胸。羃公式最初是在魏晋时期,男子遮挡风沙所用,后来女性戴羃公式则是为了遮挡面孔。女俑头戴羃公式,但并未遮盖面孔,而是坦然露出,体现出初唐的开放包容,文化上鼓励多元性,女性有追求时尚的自由。
在中国绘画史上,人马画是一个重要门类。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阴山、阿尔泰山等地的岩画及商周青铜器上就出现了人与马的图饰。真正意义上的人马画诞生于战国时期的帛画上,此后延至秦汉时期的墓葬壁画上。东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砖上的人马图像逐渐增多,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化。
到了隋唐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人马画的盛期。画卷上人马图像洋溢着一股富丽堂皇的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擅长画人马的画家不仅有职业画工、宫廷画家,还有文人画家。画家们对马匹的不同描绘手法折射了所处时代对于马的认识、理解和感受。
此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就是元代初期的赵孟頫所绘《浴马图》。图卷分为入池、洗浴、出池三个部分,描绘了奚官浴马的情景。这是一个盛夏的郊外,一泓宽阔的溪水,潺潺流淌,清澈透底,溪边河岸上梧桐垂柳,茂密成荫,有骏马十四匹,马倌九人。
人与马在画中的分布看似随意自然,其实均为画家精心构思的结果。马倌分工不同,既不相扰,又互为照应。有的牵马下溪,有的已在冲浴马身,有的则在岸边小憩;马的姿态各异,神态生动,或立于水中,或饮水吃草,或昂首嘶鸣,或卧立顾盼。赵孟頫的设色承接了唐人的青绿和重彩,但其勾线全以文人意笔,行笔虽偏工,却不失灵动逸趣。
据说《浴马图》为赵孟頫奉元武宗之命而创作。《浴马图》中有一着红袍的老胡人,又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传统中原地区与北方疆域之间分分合合的历史情结之中。
游牧地区的马
秦皇汉武以来,中原一直被视为王朝的政治中心,控制中原意味着握有正统的统治权力。北方草原文化较为稳定的文化区域包括了蒙古草原、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内陆草原民族游牧、射猎经济的特性规定了这种文化的单纯性和稳定性。
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东北戈壁滩上有一座古墓群,内有千余座魏晋古墓。其中有些墓葬为壁画墓,共出土了760多幅。在壁画内容上,以宴饮、出行、狩猎、农耕、采桑、畜牧、打场等为主的生活场面,真实地再现了当地平民百姓半耕半牧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情景。
最为有名的是五号墓出土的《驿使图》,再现了当时西北边疆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形象资料。从一号墓出土的《畜牧图》画像砖上,可窥见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畜牧业情况。画像砖从右至左绘黑白山羊和黑白牛若干只。右下方有一攒发牧童,身着交领短衣,光着脚,右手前伸成扬鞭状,袖下方朱书榜题“牧畜”二字。1600年前,河西地区的一次放牧景象被永远地定格在这幅砖画上。甘肃地处东亚与中亚的结合部,位居丝绸之路枢纽地带,这里出土的文物经常带有中亚图案的装饰风格。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团窠(音同科)动物纹刺绣剑臂属于南北朝时期的一件丝织品,以黄绢作地,用白色、绿色、深褐色等丝线绣联珠动物纹,形成六个团窠,窠内从左到右分别为:带翼神兽、孔雀、猪头、翼马、带翼神兽、翼马。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埃及安底诺伊都出土过相似的连珠翼马纹锦,有专家认为翼马纹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或中亚粟特织造体系的产物。也有专家认为带翼神兽来自西方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的怪兽格里芬,通过不同渠道最终传入中国。
从甘肃向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和广袤的草原地带,是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马成为各部落族群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装饰物。徐州博物馆所藏西汉《黄金牌饰》正面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猛兽咬斗的情景。两只猛兽双目圆睁,用利爪按住一匹马,在贪婪地撕咬。马身躯匍匐倒下,后肢扭曲反转,正奋力挣扎。据研究,这类“后蹄翻转被猛兽噬咬状”的动物纹源自欧亚草原及长城地带,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由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辽代《鹿纹铜鎏金马缨罩》可见,马纹饰从西汉一直流行到宋辽时期,直至当下。
以马为题,从江南到地中海,跨越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本展抓住了这样一个既普遍又独特的话题,讲述了一段人与自然交往的历史。自五千年前的亚欧大陆到现在,马一直与人类相伴,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从战场上冲锋的坐骑,到长短途行程中的工具,马不仅忠实地服务于人类,而且成为人与动物之间情感联结的最具代表性的纽带,它传递了人的精神,也承载了人与自然共存的价值追求。
本版图源/苏州吴文化博物馆